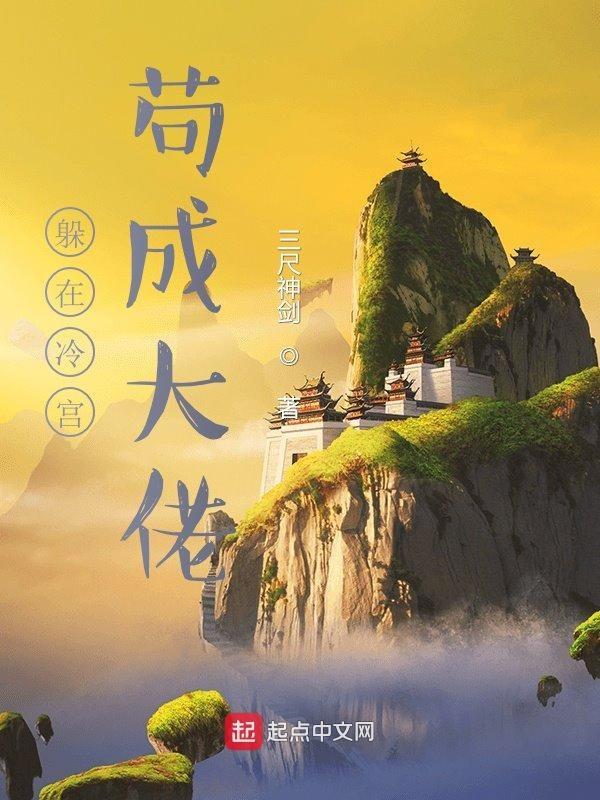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赴春潮宋妤叫什么名字啊 > 第242章 赢家(第1页)
第242章 赢家(第1页)
司厌到长安时,这群人已经喝起来了。说是最后的狂欢,‘狂欢’没有,有的只是某人的求醉,和自我麻痹。陆时屿喝酒喝的猛,其他人都在拦。司厌推门进来,有人看到他就说,“阿厌,要不你来劝劝,这小子发疯似的。”劝人司厌不会,他也懒得管这闲事,走到沙发角落里坐下,说,“他想喝让他喝。”“还是司厌懂我。”陆时屿端着酒杯过去,敬司厌酒,喝了一杯又来一杯。司厌双腿交叠坐在沙发上,掀眸看他一眼,“你喝多少我不管,我要少喝。”陆时屿端着酒杯笑,“这是有人管了?”司厌身体后仰,靠着沙发轻笑。答案显而易见。江烨瞅他笑,凑过来,“谈恋爱的感觉如何?”司厌瞥他一眼,“想知道?”江烨点头。司厌,“自己谈。”江烨说,“我又不想知道自己的,我想知道你这恋爱谈的感觉怎么样。”司厌神色耐人寻味,只说了一个字,“好。”具体怎么个好法,谁也撬不开嘴。夏妗的好,司厌只想自己知道。“谈恋爱了不起,看你那儿得意样。”江烨端了酒杯,想跟陆时屿说,‘他不给面,我给,他有人管,我没,我来陪你喝。’谁知道视线一转过去,陆时屿坐到了司厌身边,神情恍然,“以前我喝酒,南风也总管着我。”得,又开始了。这群人里,江烨和陆时屿走的算近,以前倒没多近,就是这半年的时间,陆时屿总是半夜烦他,一通一通的电话吵着他来陪喝酒。没办法,江烨缠不过他这电话攻击。陆时屿清醒时不太提他以前那女朋友,但喝到一定程度,句句都是,那就是喝杯水都能想到。‘我胃不好,南风在家里会给我煮养胃汤,就是白水,都会给我加一点蜂蜜。’江烨挺无语,‘你要想喝蜂蜜水,我让服务员给你水里加点蜂蜜。’…喝酒被管这类的话,那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听的江烨耳朵都起茧,有时候呛他,‘你到底喝还是不喝,不想喝喊我出来干什么,我不睡觉不工作的?再叨叨你那个东南西北风的,你就自个在这儿喝风。’现在一听他又开始了,立马转头。新的受害人出现。但没江烨的那些反应,陆时屿兀自说,司厌没什么情绪的听。至于有没有认真听,从他的表情里,谁也看不出来。陆时屿手里的酒杯,始终没有放下,他说,“他们都说,南风和我在一起是傍金主,是为了我的身份地位为我的钱,是为了实现阶级跨越,我知道不是。”“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她是不是真的爱我,我感觉的到,她从来没有提过要和我有什么以后,是我天真的跟她说,要让她做陆太太。”“南风不是傻白甜,不是只听男人的甜言蜜语就什么都信,我妈找了她之后,他爸爸在学校被人举报,她就知道,我妈看不上她,她和我说分手,我不同意,我跟她说,我一定会说服我妈。”“南风是被我害了,从小到大我都没看清过自己的父母,我妈宠我疼我,从小事事向着我,按我的心意来,我以为这件事,只要我用点心去沟通,去争取,她最终会为我妥协,结果就是没有沟通的余地,后来我几天不吃饭,绝食给她看,她最终心疼了,前一刻跟我说都按我的意思来,后一秒就找人,让南风出了车祸,你知不知道那天…”陆时屿说到这儿,握着酒杯的手抖了抖,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她就在我眼前被撞飞,我过去的时候,她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上都是血,我以为…她死了。”陆时屿将手里的酒一口饮尽,苦笑了一下,“最后送去医院,医生说她头上的伤不重,只是皮外伤,但腿断了,骨头粉碎,需要很多次手术才能站起来,站起来也跳不了舞了,你知道我当时的反应吗?我竟然是松口气,她失去了这么多,我庆幸她还活着。”“我后悔信了我妈的话,更后悔,没听她的话。”陆时屿看向司厌,“司厌,你和夏妗在一起,就是坏了你和徐家的联姻,你妈要是知道,会放过她吗?你妈肯放过她,徐家肯吗?任你再强大,有人要她的命,你能时时刻刻守着?”他给司厌的经验。“玩玩就够了,该分就分,别拖泥带水,生命很脆弱,意外太多,咱们本分的按着咱们的人生轨迹走,对她们,也是保护了。”陆时屿放下酒杯,改抽烟了,拿了烟盒,抽出一根,递给司厌,“来一根。”司厌没拒绝。青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司厌的脸被隐在烟雾之下,看不清情绪,他始终平静,周身气场却深沉的让人难以忽视。霍韫庭坐在沙发的另一端,无声的端起一杯酒,仰头饮尽。女人。男人似乎都逃不过这一劫。他们还能谈论,他——谈什么?谈他如何利用欺骗?他连为女人借酒消愁的理由都没有,他是玩弄感情的胜利者,应该笑,像一个赢家。霍韫庭的确笑了,是冷冷的睥睨的嘲笑。拿到想要的东西,她一定坐不住了,是不是正幻想着如何拿着证据,为沈氏正名,如何绊倒他,如何让他的双手戴上镣铐?他等着。她也该回来了。:()赴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