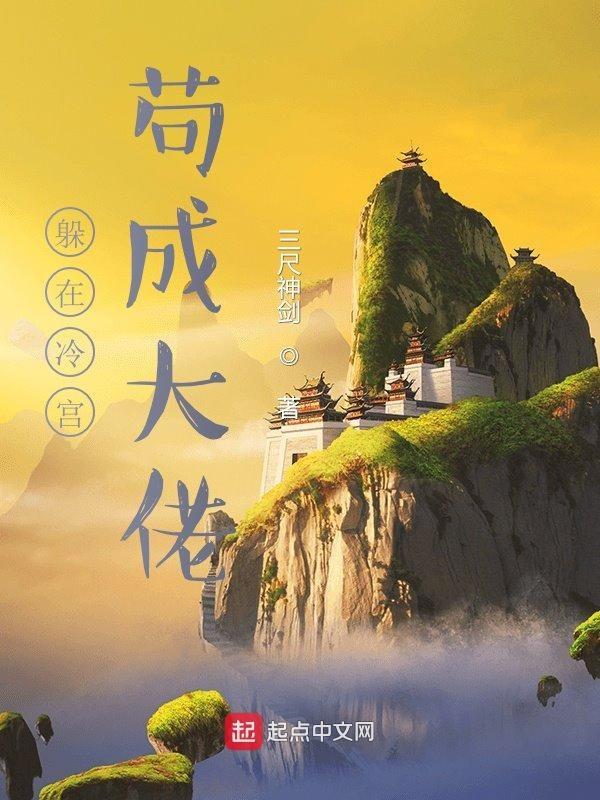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凭实力扶持反派崽崽登基 一七令 > 第45章(第2页)
第45章(第2页)
一通摸索,还真被他们找到了。被丢入水中的竟是一个捆住双手双脚,被死死捂住嘴的老者。
众人合力将他抬上来,然而来了岸上,落水的人已经昏迷倒地了。
傅朝瑜探了探鼻息:“还活着,但有些气息不稳。”
陈淮书认识这一带:“此处向南走半里地有一家草堂,里面有个坐堂大夫,医术还算不错。”
众人马不停蹄,赶紧将老人家送去了医馆。
一剂汤药下去,老者有了动静,但仍是不见醒。傅朝瑜让陈淮书留下看着,自己与众人都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傅朝瑜这衣裳还是从木工他们手里借来的,衣裳并不合身,但他出门也没有带什么换洗的衣服,只能凑合着穿。他让陈淮书帮忙照一番,自己则带着那些木匠带去了庄子。
做工的人已经找到了,监工的还是从陈国公府借来的,否则他一个人分身乏术,还真的料理不起来这偌大的庄子。等庄子修好,他一定要给陈淮书分一个大大的单间,再好好摆一桌犒劳犒劳他们。
安排好了之后,傅朝瑜才返程去了医馆。
他回来时,那位老者已经醒了,正坐在床上哭诉。
陈淮书是个多愁善感的,除了不能跟他兄长共情,跟谁他都能共情。见到傅朝瑜回来之后,陈淮书赶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抽了两下才跟傅朝瑜道:“怀瑾,这位老伯实在太可怜了。”
傅朝瑜无奈地上前与他坐在一块儿。
那老伯方才听陈淮书提起过,是他的好友带人救了自己,想必就是这位了,他忙起身就要跪谢傅朝瑜。
傅朝瑜哪里好意思受这样的大礼?一把将人扶着,眼尖地发现他似乎还伤了腿,行动很是不便,两手手背处伤痕累累,右耳处更有一道长达一指宽的裂口。傅朝瑜道:“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老伯您才刚醒,切勿大喜大悲。”
郑老伯听他这么一说,刚掩下的悲意思再次翻涌上来:“我如今活了死了也没什么两样,只是可怜我的女儿,被人抢走之后也不知如何了。”
傅朝瑜眉头紧皱。
陈淮书义愤填膺地开始解释起来:“郑老伯妻子早丧,留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前些日子承恩公府的大少爷路过他们的村子,见他女儿貌美便强掳了回府,只丢下一锭银子。郑老伯哪里要这个钱?他又不是卖女儿的。好容易打听到了对方府上的位置,这些日子几番上门要人都被那些管事小厮给打了回来,今儿守在承恩公府前可算是找到了那位大少爷,言语中间生有些口角,那狼心狗肺的竟直接叫人绑住郑老伯,要将他沉塘!”
陈淮书虽然也在京城的权贵圈中长大,但是陈国公治家有方,陈淮书自幼生活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他不能接受这世上还有此等恶毒之人。而且这般恶毒之人竟与他还有过几面之缘,陈淮书愤慨不已:“我从前在宴会上看过他,瞧着大方敦厚,没想到私下却这么猪狗不如。且他还是从咱们国子监里出来的,真是丢尽了国子监的脸。”
傅朝瑜敏锐地找到了几个关键点。
曾经的国子监监生,承恩公府的大少爷。承恩公府可是皇后的母家,是当初买下他姐姐强送进宫给皇后固宠的国舅一家。
就凭这一点,他便不会坐视不管。
新仇旧怨,正好一并算了。纵然不能绊倒承恩公府,也得给他们点教训吃。傅朝瑜追问:“老伯,你家住何方?姑娘具体哪一日被掳走的?可有目击者?”
“我家住在下塘村,上个月初七遭此大难,目击者都有,不过只怕他们也不敢出面作证。”郑老伯心如死灰之际碰到他们二人,渐渐生了些指望。这两人言谈举止都不俗,郑老伯抓着他们就如同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忙不迭地将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一遍,一字不落。
待傅朝瑜问清楚后,便让老伯暂且留在这里,等他们去国子监再商议对策。
郑老伯目送他们离开,很想再问问,那承恩公府的畜生究竟能不能被判死罪,可他最后也没能开口。
他们小门小户的穷苦人家,既没有权势也没有人脉,他便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伤不了别人一根毫毛。若是这两位小兄弟能将他女儿救出来,他便谢天谢地了,再说奢望都是空话,更不敢求坏人能够认罪伏法,谁能有这个本事呢?
傅朝瑜x等人并未回国子监,而是回了陈国公府,找了陈淮书他祖父的心腹前去打听此事原委。
这位管事是从前在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能力极强,让他来打听这些最合适不过了。
管事听完却道:“公子,那郑老伯的事情好查,但其中还牵扯了不少承恩公府的阴司,今日之内只怕没办法都查齐全。您先等两日,若是承恩公府那边查到了确切的消息,咱们立马就去国子监禀明。”
陈淮书点点头,傅朝瑜又追加一句:“尽量快些,若那位老伯没有说谎,那他家姑娘到现在还被关在承恩公府里。他说他家姑娘是个烈性子,我就怕那府里都是个畜生,回头等查清楚了人都不在了。”
陈淮书闻言兼职心急如焚,恨不得自己亲自上门去查。
虽说这桩事儿还没查清楚,但是陈淮书下意识地相信那位老伯。这事儿搁谁碰见了都会感同身受、怒不可言,等回了国子监后,陈淮书还气不过,与杨毅恬痛斥起来自己遇见的荒唐事。
杨毅恬听着也是同仇敌忾,不过等看到一动不动的杜宁后,他恍惚间竟想起来一件事儿:“杜宁,承恩公府的那个方尧年是不是从前跟你走得格外近?”
陈淮书立马凶狠地瞪着对方,还有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