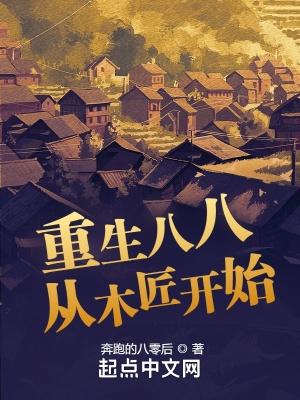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天骄纵横在线阅读 > 第40章(第3页)
第40章(第3页)
就连玉鸡卫勃然色变,喝道:“琅玕卫,你不是已撒手尘寰了么?怎会在此!”
忽然间,老人醍醐灌顶,他确听靺鞨卫说过方府出殡,琅玕卫辞世,却嘱咐府中下人烧毁其遗体,只余一盒骨灰,故无法对方惊愚行“滴骨法”。但若那与世长辞之事也只是一个假象呢?琅玕卫既能保住白帝遗孤二十余年,便断然不是个愚鲁之人。玉鸡卫也曾疑心过他尚未身死,果不其然,这个想法在此刻得到了印证。
琅玕卫非但没死,还将飞翼伏,在镇海门布下了伏兵。
玉鸡卫忽而仰天长笑,腔膛巨震。蓬莱上下竟被这一家子愚弄了二十余年!
男人付之一笑:“琅玕卫确已身死,死在了靺鞨卫眼前。此时此刻的我,不过是一介草民方怀贤!”
他举起钢剑,剑上跃动着晨曦,便似一道高举的烽烟。军吏们一呼百应,人潮汹涌,盖过了溟海的风涛声。天际显出熔金般的晖光,旭日行将东升。男人对身后的仙山吏们嘶声喝道:
“弟兄们,随我护驾!送新帝出关!”
第47章青史传名(卷一完)
转瞬间,琅玕卫与玉鸡卫杀作一团。
仙山卫之间一旦锋刃相接,便可动天骇地。琅玕卫持精钢长剑,力震六合四海。玉鸡卫则一双铁掌刀枪不入,气贯苍天白虹。一时间,镇海门前掀起冲霄尘沙。寻常军士若不慎撞进他们交搏的声浪里,轻则筋裂骨折,重则命丧黄泉,故而眼见此景,众士卒皆不敢近前。
玉鸡卫微微蹙眉,他听闻琅玕卫卧病已久,疾不可为,可此时一交手,却觉对面这男人活龙鲜健,怎像一位久病之人?琅玕卫出手凌厉,甚而比九年前更为武艺精湛,于是老者喝道:
“琅玕卫!你那病恙之态也是伪饰么?”
琅玕卫微微一笑:“敝人虽不善计谋,却绝不是莽夫。与其缠绵病榻,还是身死沙场来的好。”他怒目圆睁,忽然高喝道:“方家屈己不发二十余年,皆是为了这一天!白帝并非暴君,不过是有人颠倒黑白,将他谰言诬害。蓬莱需新君践祚,出征溟海,终至归墟,断绝连天雪害!”
男人回首喝道:“惊愚,走!从镇海门出去,乘舟至瀛洲!”
方惊愚怔怔地道:“那……爹您呢?”
他望着琅玕卫的背影,心中百味杂陈。幼时只能伏地爬行时,他曾许多次望着这魁岸的身影,琅玕卫的冷漠曾令他满怀哀戚。但现今不同了,他明白这身影是岩墙、是大楯、是挑檐,替他挡下了雨雪风霜。
琅玕卫朗声笑道:“莫怕!你爹狡兔三窟,蓬莱、瀛洲、方壶皆有涉足。去罢,爹随后赶上!”
玉鸡卫却冷冷一笑,“琅玕卫未免太过托大。你在仙山卫里不过名列第八,竟也想同老夫分庭抗礼?真是痴人说梦!”
老者弯身,十指宛若铁刀,插入土地。众人竟觉脚下震颤不已,似海运山鸣,不禁惊疑,莫非这老人能将这片地掀个翻覆么?
突然间,一枚铁箭宛若飞鸿,掠空而过,直刺玉鸡卫。玉鸡卫两手正插在地里,无暇抬起,可他却一仰脖颈,两排锯子似的森森铁齿上下一打,猛地衔住那箭。
众人正晃神,却见前方黑骊上一个戴铁面的青年手执骨弓,气喘吁吁地喝道:“放火药鞭箭!”
这确是个袭击玉鸡卫的大好时机,于是弓手们纷纷引弓,火药炸裂声不绝于耳。那青年正是楚狂,才从重伤中转愈,他脸庞极苍白,口角仍挂着血痕,身子便似一张纸片,摇摇欲坠。然而他不顾方惊愚的劝阻,寻了一匹花马骑上,冲进烟幕,向着玉鸡卫发箭。
楚狂深知这老人有铜头铁臂,与其交手时一丝懈怠之意皆不可有,不然战局会于顷刻间被扭转。
黄沙漫漫,看不清四周,便似垂地厚云一般。风烟里忽而迸出一道呼啸,是玉鸡卫弹指的声响。楚狂旋身避让,然而因头上突如其来的昏眩感动作钝了些,滑落马下。眼见着那烈风将至身前,一旁却伸来一剑,硬生生地将其阻住。
楚狂愕然地抬眼,却见琅玕卫伫立于自己身前。一柄长剑精光闪闪,仿佛会替他挡下一切险厄。
琅玕卫亦回望着他,那毅然而冷硬的目光忽如春冰一般涣释了。
“悯圣。”男人唤道。
楚狂突而一阵恍神。
他头痛难耐,自方才吃了那“大源道”教主予的肉片后,他虽伤愈,然而头脑更发混沌。他总觉得自己忘了何事。他与琅玕卫是旧识么?
男人转过身,粗粝的指腹抚上了他的面庞,目光里有怀恋、歉疚与不舍,道:
“你做得很好,是爹对不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