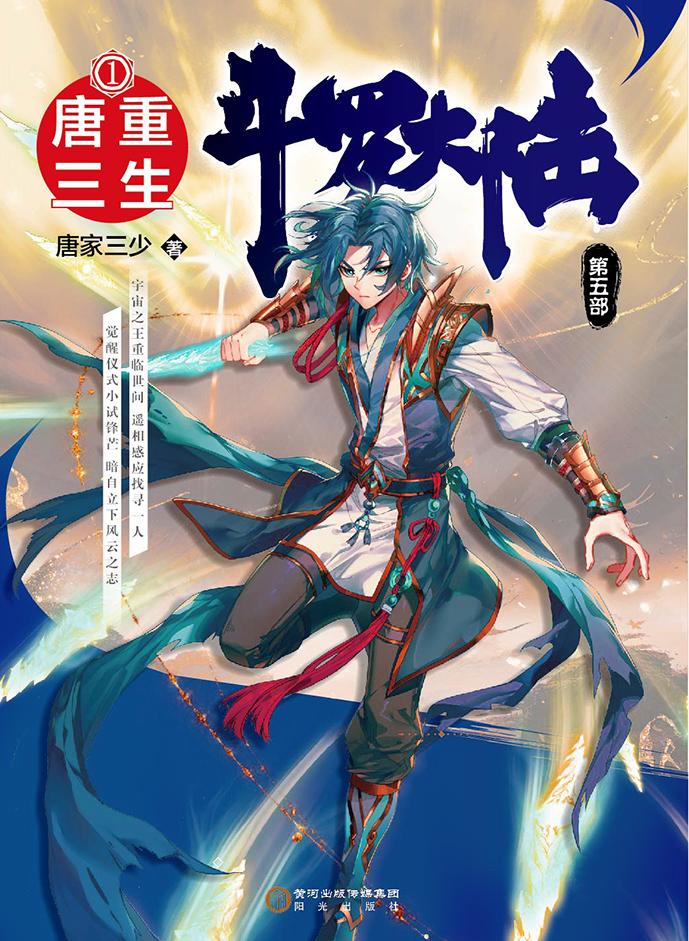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天纵骄狂txt笔趣阁 > 第99章(第3页)
第99章(第3页)
热铁绳紧缚着他喉颈,教他几近窒息。鞭抽、棍击、刀刺并无止境,他所处之地即是无间受苦的炼狱。
“毛竖地狱一劫受苦,睺睺地狱一劫受苦——”
冰盐水劈头盖脸地浇下,伤处顿如刀劈剑刺,传来钻心噬骨的痛楚。他身上发着高热,如寒暑交织。
最后,重重迭迭的诵经声念道:
“——谤法众生,于此八大地狱,满足八劫,受大苦恼。*”
剧痛如海潮般吞没了楚狂,他虽尚存一息,然而却生不如死。一刹间,他堕入无边黑暗。
不知许久,暗处里渐而有光。一盏枝形灯徐徐亮起,勾勒出一位青年的身形。谷璧卫一身玄甲,兜鍪眉庇锃亮,腰悬判官笔,坐于灯下,面容较平日看来年弱,像往昔随白帝出征时的模样。他神色平宁,问道:
“天符卫,你知晓在下为何恨你,要拿你如此磋磨么?”
楚狂站在暗处,冷冷地望着梦境里的他:“我不是天符卫,也不知你们间的恩怨。”
谷璧卫哂笑,他站起身,赤箭花在他身畔盛开,在他身后交织成一幅幅画卷。时是霜重鼓寒,车骑滚滚,碾过仙山大地;时是旷野苍莽,幽磷闪烁。“许久以前,白帝曾出征前往归墟。愈近归墟,冻毙于雪窖冰天的兵卒便愈多。为少些折损,先帝便令在下驻扎此地。”
言语间,赤箭花枝叶轻摇,幻化出一幅图景:白草黄云,石沙莽莽,原野上净无人烟,几点雁影拂过,如熟宣上不经意落下的几道闲笔。谷璧卫低叹:“望见了么?这便是最初的岱舆,荒烟蔓草。在下在此地驻守了不知几度秋,少食缺衣,身边卒子渐因风霜冻毙,最后仅余在下一人。”
楚狂沉默不语。花叶舒展,他望见一个人影独眺溟海,血肉因年岁而被磨去,英挺的背影逐渐佝偻。
“白帝与天符卫一去不返,独留在下在此地。五年,十年,还是百年?在下抱着部属的尸骨,在此地独居了极漫长的年月。可你们并未践诺,只将在下抛却于此地不顾!”谷璧卫腾地站起,神色一刹间变得狞厉。“因而在下筑起了岱舆,此地九衢三市,急管繁弦,是远胜先帝治下的极乐之地,是在下的梦景,在下的桃源!”
一刹间,千万朵赤箭花在黑暗里盛放,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勾勒出岱舆的广厦华屋、歌台舞榭。谷璧卫的影子立于其中,如独踞戏台的主角儿。
楚狂平静地道:“这里的一切皆是梦。里头活着的人也是假的。谷璧卫,你为了入这梦,动用了‘仙馔’之力。”
他又问:“实话说罢,岱舆里究竟有多少个活人?”
谷璧卫的神色突有一刹变得落寞,可却仍笑道:
“没有了。一个也不剩了。”
“百十年前,无数白帝的兵卒横尸于此,你以‘仙馔’令他们肉躯复生,神识仍为你所控,于是他们便成了岱舆的住民、黔黎。”楚狂道,目光静冷,带着一线哀悯,“可你究竟欲求着什么?造一方幻梦般的山水园子,同死人日日相伴?”
谷璧卫笑道:“在下欲建一处桃源。桃源不在陛下苦苦追寻的归墟之外,而在此地。岱輿便是在下所希冀的桃源。你呢,天符卫。你为殿下赴火蹈刀,仿佛不求有报。在你心中,‘桃源’应是何处?”
楚狂沉默不言。他从未想过这问题的答案,自打呱呱坠地以来,他的一生仿佛就被人写定了去路。“桃源”于他而言无关紧要,他的降诞只为了最后作为“白帝之子”而死去。
如此看来,他与郑得利应是一路人,只是郑得利的选择更多,而他已无路可走。
忽然间,谷璧卫的身影如被夜色洇染,悄声隐没在黑暗中。天旋地转,楚狂眼前展开另一幅画卷。
他望见了十年前的光景。那时方府云青水碧,萍花浓郁。有一着箭袖墨竹绣纹锦衣的少年正于武场中执剑起舞。方悯圣正击立刺,剑影如龙蛇而走,飘洒韵致。
风声飒飒,漫庭榆槐随之落叶,似下了一场小雨。方悯圣余光正恰瞥见墙边冬青木上有一个黑影蠢蠢而动,他飞速瞟去一眼,却见那人短褐穿结,一张小脸巴子脏污,笨手拙脚地攀在枝头。年纪看着不大,应与自己相仿。一双眼漆黑而灵动,渴盼地望着自己。
方悯圣不曾见过那小孩儿,心里惊奇,然而手上却不停,依然执剑斩削。
晚些时候前去问安时,他问琅玕卫道:“爹,白日里我在武场中练剑,曾见过有一小孩儿爬上冬青木,那便是您说的我的兄弟么?”
琅玕卫脸上现出一点笑意:“你见过他了?作何感想?”
“他太孱弱了,这样的身子,真能挑起身为白帝之子的重担么?”
“连你也瞧看不起他!”琅玕卫哈哈大笑。方悯圣嘟哝道,“我只是觉得,将来的天子应是个有赫斯之威的人。”
“身子残损,又有甚么紧要的?去仔细瞧瞧你那兄弟罢,他是大石压不断的新苗,狂岚吹不灭的火焰。看清楚后,你便会明晓,为何咱们要拥戴他作皇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