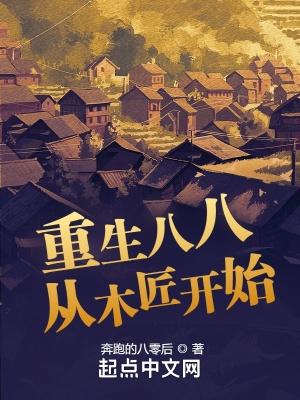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天纵骄狂txt笔趣阁 > 第91章(第3页)
第91章(第3页)
忽然间,侍卫们的神色再度回归僵木。他们纷纷自腰间抽出插子,匕尖对准自己的耳洞,狠狠刺下!一阵整齐划一的皮肉破裂声,血如飞珠溅玉,方惊愚瞠目结舌,望着他们齐刷刷自戕,两耳变作一对血洞。那萦绕在他们耳边的回响消散了,小椒的真言对他们再不起效。
一刺聋双耳,侍卫们当即抄起矛戈,再度向方惊愚袭来。方惊愚极力架御,身子却因失血而沉重,他低声对耳中的小椒喝道:
“小椒,他们听不见你的真言了,你还有其余法子么?”
小椒也慌了神,道,“他们既刺聋自己,我的声音便没法递到他们耳中,教他们听话了!我方才苏醒,神力还太弱,着实是没招儿了……”
方惊愚道,“行罢,知道你是废物大仙了。”
小椒在他耳里大叫:“我不是废物!”还忿忿地咬他耳朵,大嚷大闹,吵得他脑瓜子嗡嗡作响。
于是方惊愚横冲直撞,欲凭蛮力冲破人丛。可就在接近府门前的一刹,无数漆黑的触角自夜色里伸出,狠狠啮进他皮肉!
方惊愚吃痛。扭头一望,却见谷璧卫衣衫绽裂,铁刺一般的触角从其中探出,原来那也是只披覆人皮的怪物。当那触角刺伤他时,他突而耳鸣,谷璧卫带着笑意的嗓音如天外来声,在他脑海中响起:“小兄台被大仙操纵,神智被侵蚀,不如便教在下好好为你祛祓一番,令你清心净意罢。”
突然间,方惊愚内里如有千根冰针扎刺,谷璧卫的神识有如尖匕,生狠刺进他脑海。冰凉感很快化作烧燎烈火,焦灼五内,仿佛要将他熔蚀殆尽。方惊愚跪倒在地,气喘如牛,汗如雨滴。
小椒在他耳内惊叫,“扎嘴葫芦,完蛋啦!”
方惊愚无力应答,只觉浑身如坠炎海,筋骨遭风摧霆震。小椒惊恐道:
“他触角上带炎毒,要蚀你身心!”
方惊愚吁喘不已,只觉那入体的触角缓缓往肉里探,若有滚烫的洪流在身中决堤。龙首铁骨遇热则更热,他几尽焚身碎骨。小椒拼尽全力,欲已神力平息那灼热,然而却杯水车薪。方惊愚浑身青筋暴起,在地上打战,他痛苦之机,宁可亲手将铁骨抽出,免得其在自己皮肉里沸腾。
“还差分厘……”谷璧卫的声音仿佛自他耳畔响起,是带着欣喜的喟叹,“我就能将您当作掌中之物了,陛下。”
顷刻间,漆黑的触角一齐猛刺,血如泉涌!方惊愚惨叫一声,只觉眼前若火珠迸溅,耳畔似魑魅低语。世界变得昏花,他向黑暗里坠去。
然而正当此时,一道银虹冲破夜幕,直刺谷璧卫。
那是一支嚆矢,于黯夜里准确无误地正中了谷璧卫眼目。一刹间,一道凄厉嘶叫扯破夜色。扎于方惊愚周身的漆黑触角松动了,谷璧卫捂着流血的眼,狼狈退却。
一匹快马突而冲破人丛,方惊愚感到自己的胳臂被狠狠拽起,甩在马背上。好不容易坐稳了,却见身前是一道线条流利的脊背,跨马而行的那人正挽弓搭弦,矫若虎狼,骨弓繁弱在月下发着燐光。方惊愚喃喃道:
“楚狂……”
来人果真是楚狂。他紧抿着唇,侧脸犹如云石,在月下皎洁却冷硬。楚狂并不答话,一面夹马腹突围,冲出王府,一面控弓,白羽箭带着尖唳,像鹰隼般扑向敌手。暗无星光的夜里,他弦无虚发。方惊愚伏在他肩上,虚弱道:“你果真……来了。”
瞧得出来,楚狂早拾掇好褡子,将装箭的靫宬备好,对自己的轻举妄动留有一手。平日去马厩里闲晃时,他还特地瞅好了匹足力最健的“天马”,就待逃亡时乘上。
“正因我回回都来,殿下才胆大妄为,次次以身犯险。”楚狂冰冷地道,“殿下再这样耍赖皮,下回我便不救了。”
“那等下回……再说罢。”
方惊愚本想说些俏皮话的,但一看他神色冷峭,便也消了念头。谷璧卫的随扈在他们身后一茬茬倒下,楚狂手里挟着一束箭,施开“七星连珠”之技,仿佛瞧也不瞧便开弓,然而回回皆准中。
夜色里突而闯出一只巨大黑影,谷璧卫背手而立,仿佛飘飞在空中,触角在他身下疯狂爬搔,像舞动的蛛腿。他不一时便赶上飞驰的二人,对楚狂笑道:“天符卫好忠心也,回回都赶着来救驾,简直同陛下是如漆似胶,形影不离。”
楚狂默然不语,对他连发数箭,然而这回谷璧卫似有所备,触角飞动,一一将箭矢擒下。谷璧卫忽而冷笑道:“真是蚍蜉撼树,也不知你是凭甚取得的天符之名?白帝无眼,若论威势、气力,而今的在下比那时的你长上许多!”
“我不懂你在兀自记恨什么,但我知老叫错人名姓很是失礼。”楚狂说,神色淡冷,箭出如霹雳惊雷,“我俩不是白帝同天符卫,是两个过路岱舆的海客而已。”
谷璧卫微微一笑,也不同楚狂多辩,突而启唇,从其间喷吐出一股怪声。
那声音好似钟鼓梵音,在人耳畔訇訇作响。楚狂闻之,颊边不由得淌下一道冷汗,只觉眼前如黑暗暗云迷四野,头上若有钢针扎刺。
于是他知晓这大抵是谷璧卫用以操控旁人的真言。他服食过太多“仙馔”,极易受这魔音浸染。然而他连昔日被剖膛破肚的苦楚都忍下来了,定一定神,很快将那魔声撇到脑后。谷璧卫见他仅是脸色略白,却仍不为自己所用,也是惊奇,索性将触角攒射而出,直刺楚狂。
“当心!”方惊愚冷汗涔涔。方才他已遭袭过一回,深知这些触角的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