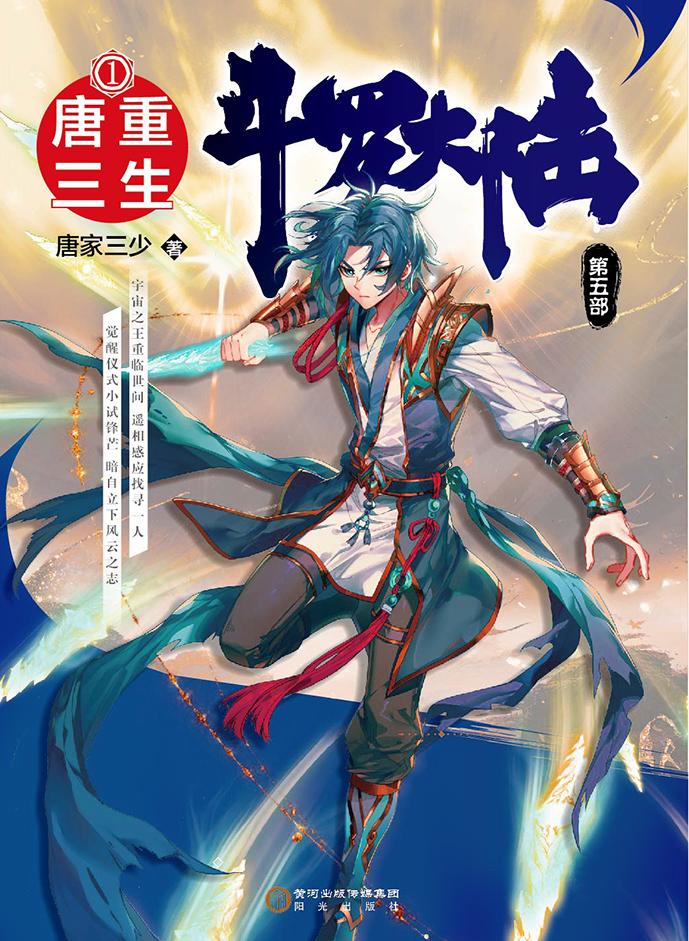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天纵骄狂txt笔趣阁 > 第27章(第2页)
第27章(第2页)
平日里爹也鲜少与郑得利说话,他的心情便似一阵狂岚怒涛,来得极快,去得也疾,变幻莫测,先前能因郑得利去了醉春园一事而对其狂吼怒叫,过后却又老僧入定般枯坐了三日,静得似一只坟包。而此时,爹将他唤入屋中,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天象变了。”
“什么天象变了?”郑得利好奇地发问。
他爹冷冷地道:“你不是耽于女色,不愿随我学天文么?怎么今夜倒发起兴致来了?”
郑得利的脸煮熟的龙虾一般红,道:“爹!我到醉春园去时没嫖妓,去找的那位是小倌!”话一脱口,他又觉不对,且觉得爹瞅着他的目光愈发不对劲了。
他爹哼了一声,起身到杉木架子上捧了一只粉彩盒,从其中取出一枚骨片,交予他。
郑得利接过来一看,只见那骨片斑斑驳驳,似刻着许多蝇头小字,却皆是不认得的记符。他爹说:“这是先祖留下的骨董,其上记载着蓬莱的历史,你若这般有闲情逸致在外摆手晃脚,倒不如沉下心来,好好解读。”
郑得利最头疼这些同史书、天文相干的物事,他爹昔时教他算经,书上都是些令他发昏的数字。至于史书,他家因世代供职于天文院,家中倒藏有些,也不算得违了律令。只是那史书上用的字多是契文,看得他脑热眼昏,倒不如学岐黄之术来得清净,若有小病小痛,也能自行解决。
于是他接了骨片,含含糊糊地应了两声,便欲蒙混过去,谁知爹此时又道:
“得利啊,你如今正被卷入一股湍流中,抽身则泯然众人,苟延残生;投身则慷慨就义,轰轰烈烈而亡。”
他爹总爱说这些神神道道的话,兴许是星象瞧多了,真以为自己能天人交感了。郑得利听惯了这些话,便也随口应道:“横竖都是死,就没好一点的死法?”
他爹又道:“人终有一死,只是途经之景不同。你的命途也记载在骨片上,去解读这一切罢。”
说这话时,月光流淌在他爹那褶裥渐显的面庞上,郑得利忽而无端地心惊,爹的身影像入水墨晕一般,在他眼前渐渐迷蒙。再眨一眨眼,那身形忽又似一尊缄口不语的神像,直挺挺地矗在眼前,只是多了些悲天悯人的意味。郑得利敛了散漫心思,拿着骨片,沉重地点了点头。
不知为何,他忽有一种预感,这个夜晚将在他的人生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便似那深铭在骨片上的契文一般,其意义将在许久之后昭然若揭。
郑得利捧着骨片,慢慢起身,正要离开,却听得身后的爹忽而道:
“你想离开蓬莱么,得利?”
郑得利吃惊,匆遽回身,摇头道:“跨越蓬莱天关可是死罪,不孝子怎敢肖想!”
爹说:“是啊,时机还未到,你的命星还未发光。”
郑得利最后回头看了爹一眼,那身影坐在青砖上,沐浴在水银样的月色里,与漫天熠熠繁星相拥,却显得瘦弱而枯寂,仿佛被人世遗弃。他的心里忽而不是滋味,再未回头,快步离去。
————
方惊愚回到了方府中。
昨日他回了方府一趟,知晓了关于他身世的诸多密辛,在春生门外同“骡子”接头后,他还是放弃了出蓬莱天关的念头。蓬莱这片土地上承载了太多他的回忆,他不能这样轻易离开。
然而家中的两人却全然不知这一切。小椒连觉也不及睡,拽着他在堂屋里坐下,烧了火盆,命他坐在马扎上,自己在他面前打转,质讯犯人的模样,怒眉睁目道:
“扎嘴葫芦,你怎么一声不吭便要逃啦!”
方惊愚沉默不语,低眉垂眼,火光在他脸上明灭,愈发令他显得心事重重。
小椒急得狗咬尾巴一般团团转,叫道:“我知你家人待你不好,可你也不要回趟老家便寻死觅活的。天关是你能闯的地儿么?你敢闯一次,重则死罪,轻则被捉去同楚长工一同烧火!”
楚狂正在一旁用木枝捅着炭灰,闻言桀桀狂笑,叫嚣道,“烧火有甚么不好的?暖和极了,还能偷着煨两只白薯呢!”
小椒劈手夺过他的烧火棍,在炭灰里捅了两下,果真发现了两只白薯。
她气得扔下木枝,夺过其中一只,也不管楚狂的恶语唾骂,用两指拈着皮,迅速地剥净了,一面抽着冷气一面大啖起来,然而眼眶依然是红红的,对方惊愚道:“死葫芦,我说的话进你耳朵没有?你若走了,这家里谁来做饭?谁来替我补衣裳?谁来帮我刷马?”
楚狂说:“我都会做。”
小椒想了想,发现这些事确实不是非方惊愚不可,然而却依然心结未解,泪汪汪地在屋里转着圆,一副气急噎着的模样。这时却轮到楚狂跳起来质问方惊愚了,他一面气急败坏地吃着烤白薯,一面口齿不清地怒斥方惊愚:
“你既要走,怎么不知会我一声?你心里还是有出蓬莱的念头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