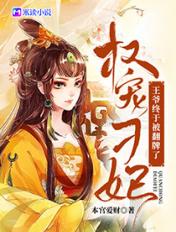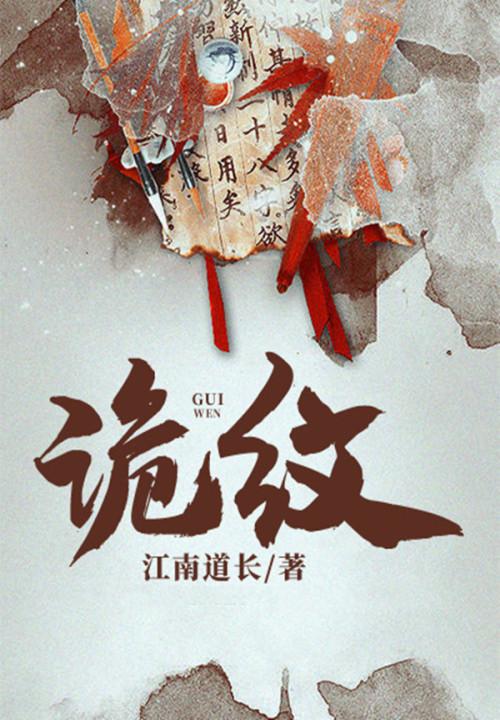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可以蹲你吗 > 5060(第2页)
5060(第2页)
他神色岿然,不偏不倚道:“陛下多虑了。既是明珠,怎会蒙尘?”
皇帝道:“此言差矣。朕为天子,也有老眼昏花的时候,留着一副赝品当宝贝。青天虽高,难免浮云遮蔽。近来听说坊间流传一些新奇话本,也不知写些什么,驱魔司带人封禁了全长安的书摊,还抓了许多文士,惹得民间怨声载道。”
杨玉文道:“话本子里都是些诽谤朝廷的逆悖之词,不堪入陛下耳。”
皇帝道:“这么说,你知道这事。”
杨玉文浑身一僵,陡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皇帝眯起眼睛,流露出几分不怒自威的气度,道:“本朝开国至今,广开言路,从未兴过文字狱。烧书烧不完天下笔杆子,堵嘴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连朕当年推广新政,民间都颇有微词。而驱魔司却议论不得,不知这天下究竟是姓柳,还是姓杨?”
杨玉文受此诛心之论,当即跪地,叩首道:“臣万死!”
头磕在地上发出重响。
皇帝高坐龙椅,垂眼望着诚惶诚恐的杨玉文,喜怒不辨。
满殿鸦雀无声,静得落针可闻。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
皇帝叹了一口气,摆摆手。杨玉文是他看着长大的,也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皇帝对他的性子再熟悉不过,话说到这份上,终是心软。
“朕知杨家三代忠良,天地可鉴。十年前你姑姑为救驾死在崇明殿外,五年前国师于任上负伤,不得已病退,朕痛失臂膀,至今扼腕。幸亏有你撑起杨家门楣,执掌驱魔司。才没让底下这一摊子乱起来。”
谈及往事,皇帝目光沧桑,心绪绵长。
杨玉文始终伏低着头颅。
皇帝亲自下殿台,扶起了长跪不起的臣子,握住他肩膀,道:“玉文,这些年你的辛劳,朕都看在眼里。朕从未疑过你的忠心,可人太年轻,容易栽跟头。如今四海升平,依旧有妖魔作祟,你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杨玉文掷地有声道:“臣为陛下赴汤蹈火,马革裹尸,九死未悔。”
皇帝话锋一转,道:“担子这么重,就别把手伸得太长了。”
杨玉文道:“臣知罪。”
皇帝道:“原也不是什么大事。书摊该开的开,人该放的就放。”
杨玉文背后冷汗流了出来,道:“谨遵陛下旨意。”
皇帝岔开话头,并未揪住此事不放,随口道:“十年之期将至,长安大阵要换了吧。”
杨玉文道:“是。”
“日子定在哪天?”
“九月初九。”
“换阵不是小事,”大阵关乎长安全城,须得谨慎。皇帝沉吟道:“老九,你替朕去看着吧。”
柳章走到杨玉文身侧,与他并排跪倒,“臣领旨。”
皇帝道:“玉文可有异议?”
杨玉文无话可说,皇帝给了他一个台阶,他只能下来:“陛下安排妥当,臣无有异议。”
皇帝捋着胡须,颇为欣慰,笑道:“那就好,有你们两个在,朕大可放心了。”
片刻后,皇帝午休。柳章与杨玉文跪安告退,从崇明殿出来,天有些阴沉,眼瞧着是要下雨。二人并肩行走在皇城下。宫墙深深,风雨欲来,吹得人袖袍猎猎如纸鸢。
杨玉文忽然笑了起来,道:“九殿下好手段。”
柳章道:“杨大人此言何意?”
杨玉文道:“算无遗策,环环相扣,我是一丝也没料到。”
柳章在玉清观忙活了几天,才回来,被急召入宫。皇帝说他字好,让他写两幅字。柳章并不知道皇帝有何意图。字还没写完,杨玉文便来了。柳章隔岸观火,到底是听出敲打意思。驱魔司独大,无法无天,皇帝要抬举柳章跟杨玉文打擂台。
事发突然,柳章不可能抗旨,一步步下来,站到杨玉文的对立面去。
杨玉文吃了个哑巴亏,怎么可能不恼火。长安大阵由驱魔司一手创立,换阵之期在即。空降柳章来主持大局,杨玉文多年辛苦,直接被柳章压了一头。
“初九那日,风景会很不错,还请九殿下切莫迟到。”
杨玉文咬牙切齿甩下这句话。
柳章神色不变,淡道:“多谢杨大人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