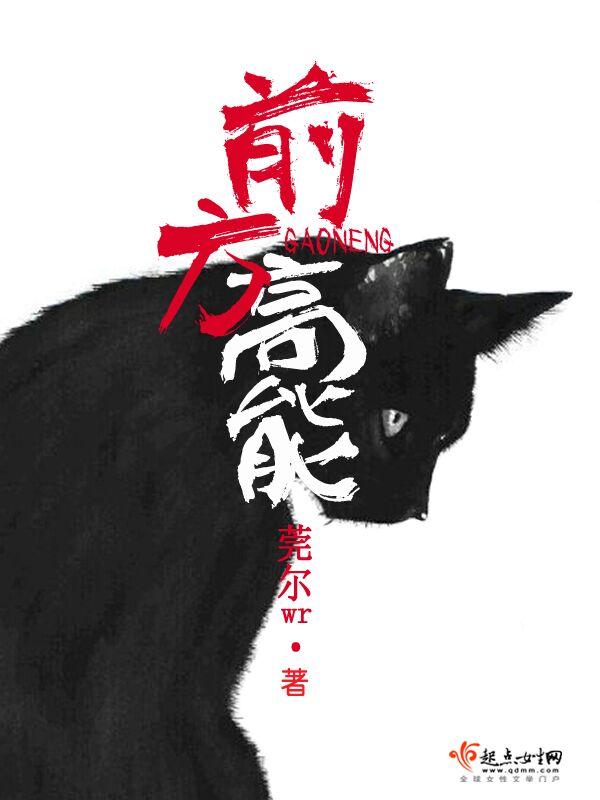秃鹫小说>江南老裁缝家纺 > 2第 2 章(第2页)
2第 2 章(第2页)
nbsp;nbsp;nbsp;nbsp;林秀水将软刷浸到水盆里,擦干手,从桌面边顺着摸一遍,确保没有脏污。
nbsp;nbsp;nbsp;nbsp;又把要熨的细麻布拿过来,确认正反面,反面朝上,确定经纬线,边扯边跟顾娘子解释:“熨布要有水,细麻布喷水不匀,拿刷子蘸水梳几遍,湿了就能熨,到时再上熨斗。”
nbsp;nbsp;nbsp;nbsp;顾娘子对此不言语,只是摸摸她那檀色素缎夹衣,实则挺满意,虽然瘦小,至少眼前这个不喷口水。
nbsp;nbsp;nbsp;nbsp;小春娥倒是捧场地低低叫了声,用火钳子夹着炭往铜熨斗里放,嘴里喊着炭好了。
nbsp;nbsp;nbsp;nbsp;这熨斗又称火斗,全靠炭火红了圆铜底,加热来回熨平整。
nbsp;nbsp;nbsp;nbsp;只是不好用,熨斗的斗身跟斗柄连起来是笔直的,都不往上翘,越直则握得越紧绷。
nbsp;nbsp;nbsp;nbsp;林秀水不喜欢这种熨斗,它会跑灰到布上,此时无比想要她记忆里的电熨斗。
nbsp;nbsp;nbsp;nbsp;尤其铜熨斗很难把控火候,一不留神,熨布就成了炙肉。
nbsp;nbsp;nbsp;nbsp;在有两双眼睛盯着的情况下,林秀水依旧不慌不忙的,要了一口粗瓷大碗,盛满了水,又要把剪子,裁一小片麻布反着放桌上。
nbsp;nbsp;nbsp;nbsp;小春娥沉不住气,凑过来说:“瞧你这架势,跟从前的娘子都不一样,这是要做什么?”
nbsp;nbsp;nbsp;nbsp;“把水烤热了喝,”林秀水逗她,见熨斗里的炭红灼灼的,把铜底顺着水面刮一下,立马响起“嗤”的一声,温度大概到一百二十。
nbsp;nbsp;nbsp;nbsp;她梦里的东西还要日夜苦练,才能靠听声辩温度,等水泡变得细密,有了叽咕声,那就往上升了十度,是熨麻布最好的温度。
nbsp;nbsp;nbsp;nbsp;林秀水谨慎得很,这温度她得在小布上先试一遍,再放到麻布上,平熨不拉扯。
nbsp;nbsp;nbsp;nbsp;只听噗噗噗的声响里,原本那皱巴巴的麻布,在熨斗下逐渐变得极为平整。
nbsp;nbsp;nbsp;nbsp;反熨再正面平烫,那麻布都像是生了光泽感。
nbsp;nbsp;nbsp;nbsp;林秀水熨布一气呵成,加炭减炭,刮熨刷水,没有停顿,仿佛眨眼间那布就自个儿服帖了。
nbsp;nbsp;nbsp;nbsp;“从临安城来的?你在帐设司做过活?”
nbsp;nbsp;nbsp;nbsp;顾娘子这才细细打量她。
nbsp;nbsp;nbsp;nbsp;姨母叫她出门就说是桑桥渡的人,怕别人笑话她,可林秀水才不怕,她将熨斗放在空炉子上,蹲在那抬头道:“从上林塘来的,没去过帐设司。”
nbsp;nbsp;nbsp;nbsp;临安的四司六局她是知道的,帐设司专管张盖帷幕、桌布、门帘、屏风等物,自然要有人手熨烫。
nbsp;nbsp;nbsp;nbsp;小春娥心直口快:“怎么会,上林塘种稻的,米行里多是你们那出的米,应该往米行里去才是。”
nbsp;nbsp;nbsp;nbsp;正经人家种稻能出两三石,林秀水一亩地出一石,那还是肥田,她也不大分得清米好坏,除非煮熟了叫她吃一口。
nbsp;nbsp;nbsp;nbsp;林秀水就说:“我没那本事。”
nbsp;nbsp;nbsp;nbsp;“那你这熨布本事呢?”顾娘子追问。
nbsp;nbsp;nbsp;nbsp;林秀水跟她如实说了,不管是铁熨斗,还是铜制的,她都买不起,便去问人家富户家要不要熨布,还熨坏过一些布料,赔了几笔钱。
nbsp;nbsp;nbsp;nbsp;她熨了两年,对各种布料自然也摸清楚了脾性。
nbsp;nbsp;nbsp;nbsp;顾娘子又细说了工钱,便道:“这会儿天色晚了,你明日辰时边上过来。”
nbsp;nbsp;nbsp;nbsp;这话的意思已然明了,林秀水欣喜,却不急着走,要把布理了,炭夹到炭火甏(bèng)儿里,剪子放好,将木桌收拾齐整了再走。
nbsp;nbsp;nbsp;nbsp;一出了门,林秀水搓搓手里的汗,又摸摸脸,才露出小小的笑。
nbsp;nbsp;nbsp;nbsp;今日天色不好,像湿柴熏出来的烟,风刮不散,人都步履匆匆,闪眼而过。王月兰赶过来,问她今日怎么样,林秀水说:“回去就能宰鸡的好。”
nbsp;nbsp;nbsp;nbsp;她看外头的水,只觉得桑青镇的水真好,很肥,都似飘着油花。
nbsp;nbsp;nbsp;nbsp;“有说月钱多少没,领到了你再想着吃,”王月兰要务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