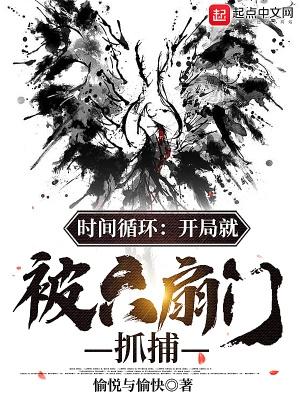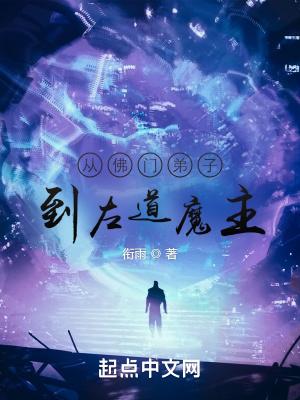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mobi > 第79章(第2页)
第79章(第2页)
始建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长安,宣平门外。
王莽正在雨中亲自祭祀路神,以饯别一支军队,为首的是太师将军王匡、更始将军廉丹,他们准备赴关东远征樊崇军。王匡是王音之孙、王舜之子,还很年轻;廉丹是新朝老将,廉颇后人,经验丰富,两人位高权重,带领十万大军出征,寄予了皇帝一举荡平关东的厚望。
此番出征,不仅有军事意图,还要兼顾赈灾。前些日子田况给皇帝的上书提到,洛阳以东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两千钱,来自关东郡县的报告上也惨痛地说“关东人相食”。因此,他们还要在关东打开粮仓,赈济饥民。
雨下得很大,把军人的衣服都淋湿了,给原本雄壮的出征仪式蒙上了一丝悲壮和不祥的色彩。有老人哀叹地说,“是为泣军!”14
但真正要哭泣的,其实是饥民。王莽虽然取消了山泽之禁,打猎捞鱼不用交税了,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更荒诞的是,他派人到全国各地传授一种方法,据说把草木煮成酪能够充饥。
关东的饥民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出关的王匡、廉丹十万大军,又加重了关东的局势。正如田况所预料的,大军所过之处,比流民更甚。以至于关东有谚语说:
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15
王匡比赤眉可怕,廉丹比王匡还可怕,这个链条透露了廉丹的残酷。但战争哪有不残酷的?这侧面反映了廉丹比王匡更像一名将军。自四月出征,王匡、廉丹到了定陶,还没有与樊崇军作战,皇帝的诏书先追了上来。
王莽斥责廉丹,“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16。这话说得很重,但其实就是催促廉丹尽快荡平关东,不要蒙上贪生怕死之名。
廉丹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但皇帝直接催促进兵,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把诏书拿给自己的下属、将军掾冯衍看。冯衍是汉元帝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之孙,冯昭仪的孙子是汉平帝,算起来,冯衍和汉平帝是兄弟。因此,冯衍对王莽是很抵触的,看到诏书,就劝廉丹不要出战,而要拥兵于大郡,招降纳叛,以待时变。
廉丹不敢,大军继续前行,到了睢阳17,冯衍又一次劝说廉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延宕就没有机会了。
廉丹最终没有听从冯衍。他与王匡在冬天时抵达有盐亭,就是改名前的无盐县。这里已经被一名叫“索卢恢”的叛军占据。王匡、廉丹迅速将其攻克,斩首万余级,取得了一场大胜。
王莽很高兴,派中郎将劳军,将廉丹晋爵为平均公。王匡受到激励,侦知有一支号称赤眉的队伍由董宪统领,驻扎在梁郡,就很想乘着士气高昂,一举击破。董宪其实和樊崇军没有直接关系,是自立的一支武装,只是以赤眉为号。廉丹却认为,刚打下无盐,士兵都很疲劳,应该休养一番,恢复士气。王匡不听,自己带兵出发攻打董宪。
见此情景,廉丹不得不紧随其后,在成昌县18,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王匡、廉丹惊奇地发现,这些人之所以叫赤眉,是因为他们把眉毛染红了。而且,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早有准备,以逸待劳。一番激战,王匡、廉丹兵败。
王匡见状,主张尽快逃走。廉丹心里如何想已经不得而知,但面对一个冒进失败又没有担当的同僚,该是非常无奈吧。他派属吏把印玺、符节等重要的凭信都交给王匡,说:
小儿可走,吾不可!19
称王匡为“小儿”,有愤激指责的意思,但也可能是把王匡还当作孩子。而他不走的理由,想来该和王莽的那封诏书有关。廉丹交代完后事,带领残兵力战而死,果然实现了诏书里“捐身中野”的话。
廉丹的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位将军见到主帅阵亡,都说“廉公已死,吾谁为生?”20纷纷骑马冲入赤眉军阵,全部战死。由此可见,廉丹的确是一个颇得人心的合格军人,既不辱没先祖廉颇,孙子廉范也能因为贤能仗义在东汉扬名天下。王莽派他出征,不无识人之明。
冯衍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侥幸逃出乱军,向河东逃命去了。
得知廉丹阵亡,十万大军只剩下王匡的残军,王莽悲痛不已。但他仍然不重视田况的忠告,继续选拔将领东征。这时,早就被他晾在一边的国将哀章站了出来,主动请缨去东方支援。
哀章虽为四辅,手中却没有什么权力,被认为是王莽最轻贱的人。而且他贪恋禄位,有贪赃徇私之事。王莽得知后,没有惩处他。正好当时给四辅配备副手,也就是太师羲仲、国师和仲、太傅羲叔,以及国将和叔。而这位国将和叔,名义上是哀章的副手,实际上是派来监视他。几年来,哀章在长安过得不舒服,想去关东立功,也躲避监视。
王莽同意了,令哀章带兵驰援王匡,又派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带兵十万赶赴洛阳,很快就重建东方防线,但防线已经萎缩到洛阳一线,再往东的地区,只有王匡和哀章的弱旅。赤眉军则从东海、琅琊诸郡,到楚、沛、汝南、颍川诸多郡县,四处转进,与各地郡县的政府军战斗,胜多败少。皇帝在东方战场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