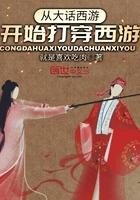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王莽及其时代 > 第98章(第1页)
第98章(第1页)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17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王莽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1 《后汉书·刘玄列传》,第470页。
2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11页注引《续汉志》。
3 今甘肃平凉泾县一带。
4 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5 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6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4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