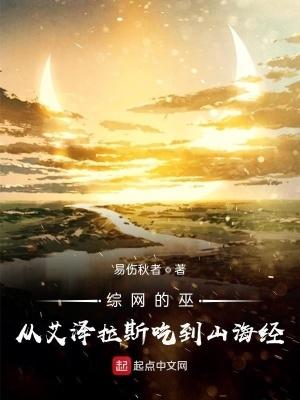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王莽及其时代 > 第57章(第1页)
第57章(第1页)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进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点: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文经学的基础并不牢靠,古文学不逊于今文经学。
第二,今文经学虽然师法家法明确,但最初都是口口相传,现在古文学连文献都找到了,文献难道不比口传更可靠?
第三,今文经学里,穀梁学和公羊学差别不小,也有矛盾之处,尚且都可以并立学官。凭什么说古文学就没有道理立在学官?
从后世角度看,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哲学,古文学近乎史学或文献学,两者的政治品质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口传真有可能比文献更真实。但在当时,这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的批判书一出,朝野大惊。十四博士们震怒,桓谭等人为之雀跃,谁都没料到刘歆敢将对官方经学的不满予以公开化。说到底,刘歆这封信反对的并非今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垄断学官这件事,原本儒学内部的讨论,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事件。
丞相孔光就不必说了,此时已经迁任大司空的师丹为之大怒,斥责刘歆破坏汉家旧制,诋毁先帝;光禄大夫龚胜并非博士,也非朝官,但他凭着名儒的身份,也跳出来反对刘歆,龚胜刻意上书劾责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请求领罪退休。龚胜能有什么罪责?他说这样奇怪的话,无非是依仗“学术权威”的身份,摆出没有教育好下一代的姿态,故意不给年轻人脸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