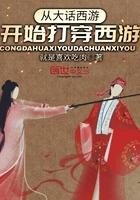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刘愔夜观天象的“白衣会”果然发生了。只可惜,不是皇帝,而是皇后。
因为那封书札,王莽严令王临待在洛阳,不得回到长安奔丧。他要弄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会如此害怕。既然那封信是写给皇后的,不妨从皇后的身边人查起。
皇后下葬,王莽立刻对原碧等皇后的侍女、王临在长安的家人严刑拷讯。原碧想来是承受了重刑,最终交代了王临和她私通以及弑父的密谋。这可不是当年王宗所谓的谋反案可比:王宗只是青春期少年的叛逆和幻想,王临却是实打实要弑君弑父的伦理惨剧。
面对审讯结果,王莽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当年杀王获,杀王宇,都是由他来掌握主动权,并作为实践儒家经义、模仿周公的重要动作。而王临反过来要弑父,说明儿子不甘心束手待毙,宁可冒犯最重要的伦理也要求生。
这反而令王莽有所胆怯了,他失去了把杀子包装成大义灭亲的那种自信。相反,他秘密处理这件事。把参与审讯、知道王临弑父图谋的治狱使者、司命从事等全部悄悄灭口,就地埋在监狱里。这些冤死的司法人员的家属发现亲人集体失踪,上班之后再也没回家,大概能猜到什么,但既不敢说,也不敢问。
至于王临,王莽决不可能让他活着,就赐给毒药。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死的王临,终于做了一件王氏子孙人人都想做但从前不敢做的事情:不服从。
他不服从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父亲送来的毒药,而是以利器刺死了自己。仅存的王安、黄皇室主如果知道王临以自己的方式赴死,悲痛之余说不定还会嘉许呢。
灭口了知情人,逼死了儿子,王莽仍然要粉饰,说王临不遵循符命,在统义阳王的位置上没能得到上天护佑,以致夭折,实在可怜,谥号和王宗一样也是“缪”。
同时,他又指责亲家刘歆,说:
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15
如此看来,王临招供了夜观天象的事情,但没有牵连刘愔。可王莽觉得,如果把刘愔当成始作俑者,那么儿子谋杀自己的伦理伤痛可能会好受些。
刘歆没能保住爱女,刘愔也自杀了。
这是新朝建立后,刘歆失去的第三个子女,他对王莽最后一丝尊崇、好感、旧日情谊也荡然无存。他担心自己也会性命难保,就像当年的甄邯,也在政坛上渐渐消沉下去。
第一家庭的这场变故后,王莽好不容易成年的四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颇荒忽”的王安了。
失去了母亲兄弟,王安估计也早就活够了吧,就在王临两口子死的这个月,王安病死。王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去世。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要疯掉的女儿。七百多年后的那首诗,到此终于可以完结了: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后世有人评王莽说:“其意但贪帝王之尊,并无骨肉之爱也。”16
这句话后半句正确,前半句可商,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不管怎么说,继承人终归是大事。王莽还有其他孙子,有侄子,噢,还有“遣就国”期间和三个侍女私生的四个儿女。他以刚去世的王安的名义,把这些私生儿女们也都接到长安。
但王莽没有再立太子。
其实,立与不立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再有两年,他和他的皇朝就要覆灭了。
《汉书》没有刻意言说皇帝的“性欲”,但他和三个侍女生下四个孩子,与皇后的侍女通,其他类似事件可能还有。这说明王莽是一个性欲旺盛、内心压抑、急需纵欲来调理的人。现在,第一家庭已经不存,他不顾内忧外患已使新朝摇摇欲坠,萌发了组建新的第一家庭的想法。
就在第一家庭四个成员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作阳成修的郎官,献上一条符命,说如今没有“天下母”,要再立皇后才行。天下都知道现在禁止献符命,但对这一条,王莽却欣然接受,所以有可能也是他亲自授意。
朝野臣民,在天下已经兵连祸结之时,眼睁睁看着皇帝一面大放悲声,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把自己死去的子孙葬在里面;一面兴奋地派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各地,访求淑女,准备立新的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