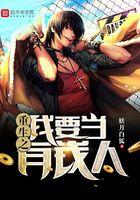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第三,发掘现任地方官中的儒学人才,优秀的担任左右内史等京畿地区官员的属员,较一般的也担任各郡太守的属员。
这几乎重建了汉朝的官员选拔体系,保证儒生被源源不断补充到中央和地方的中低级官吏行列,随着这些人的正常升迁,汉代朝野的儒家官员甚至高官将会越来越多。
这正是董仲舒曾经想做但始终没有做到的事情33,也是公孙弘了不起的作为。
董仲舒七十岁那年,允许他返回长安的诏令到了,不知道是皇帝记起了他,还是公孙弘见到那封信后决定放过他。
辞别胶西王,董仲舒松了一口气,或许胶西王也松了一口气。
返回长安的路上,正值冬季,一路上都在下大雪。雪势之大,是皇帝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经过的郡县,总有贫民被冻死。董仲舒知道,这灾异预示着将会掀起可怕的大狱,但他再也不敢说出这个秘密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向皇帝上书,求皇帝准许他致仕。
皇帝答应了,又令张汤登门向董仲舒学习如何以儒术来审案。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写下二百三十二个案例,详细解释如何用儒术来平决案件。从这一点上说,董仲舒所做的与公孙弘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儒术融入汉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公孙弘也有《公孙弘》十篇,记录他以儒术理政的经验,据说内容极为精要,每个字值百金34。
他们两人的差别,是作为经师拥有的政治德性不同。
故园仍在,木繁草长。董仲舒想起昔日“三年不窥园”的往事,想起汉景帝时,他还算年轻,有一日,天朗气清,他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下报称有客人来访。来者脱履登堂,风姿绰约,令他精神一振。主客交拜行礼,分别在席上坐下。面对董仲舒这样的海内名儒,此人并不苟且,仪态颇为大方,谈吐十分不俗。他们谈起儒经的精微奥妙,更是多有相契之处。董仲舒很想引为知己,又颇觉可疑,因为他感觉此人对自己非常熟悉,若非曾经同门共学、朝夕相处,绝不可能有如此默契,然而,他从未闻说此人大名。
日光依然灿烂,照得门外白花花一片。
客人忽然说:“噢,要下雨了。”
董仲舒一怔,恍然大悟,笑着对客人说:“我晓得了!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
那人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绰约的人形迅速朽坏下去,旁边侍奉的仆人吓得把手中的漆盘掉到了席上,眼看那来客化作老狐狸的模样,仓皇跳出前厅,不知去向。35
而现在,他每晚都到园子里,仰首观天象变幻,个中玄机只有自己能领会。不久,他听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两王皆自杀。而主持这次谋反大案审理的,正是当年险些害他被杀的高足吕步舒和时常求教的廷尉张汤。吕步舒和张汤以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为蓝本,审理两王之案,最终有万人死在这场大案中。印证了上年冬日大雨雪所的寓意。
夜观天象,他还发现北极星旁的三颗星突然有一颗变得极暗,这预示着三公中有一人即将死去。而此时,御史大夫李蔡刚刚被免,太尉一直空缺,三公中唯有丞相公孙弘在任。果然第二年公孙弘薨于任上。
董仲舒是否可以理解公孙弘?
他或许能理解,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灾异论说的道理,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36
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然无法赞赏公孙弘。理解,但决不赞赏,不是因为两人命运殊途,而是董仲舒仍然深深陷落在政治的困惑里。进入帝国时代的儒学,从理想上看必须驯服帝王,但是真的可以做到吗?逐渐“经学化”的儒学,随着地位的升高,将来还有动力去批判驯服帝王吗?
多年以后,刘向、刘歆父子争论董仲舒的地位,父亲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儿子刘歆却很不以为然,认为充其量只是“群儒首”。从董仲舒的毕生事业来看,刘歆所言不虚,他的确没有什么王佐之才;但倘若以理想主义来观,董仲舒岂又只是儒生之首?假如董仲舒遇上王莽,该会怎样?
注释:
1 《汉书·扬雄传》,第3584页:“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2 即汉朝的大鸿胪。
3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语,第30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