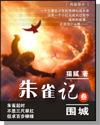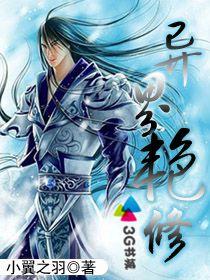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 > 第48章(第2页)
第48章(第2页)
2.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5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6。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7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8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