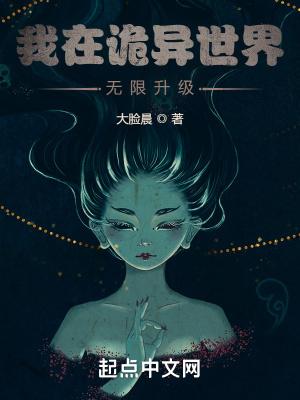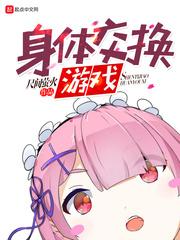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87章(第2页)
第87章(第2页)
但对王莽而言,即使侮僈神灵,那也是汉家神灵,与自家无关。汉家神灵确实也没能护佑王政君多久,到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二月,八十四岁的王政君去世。这个年龄在21世纪也属于高寿了。
遵照王政君遗愿,她与丈夫汉元帝合葬渭陵。但依新朝法度,她是新室文母,不必是汉家媳妇,因此王莽下令以汉元帝配食她的宗庙,并在她和元帝的坟墓之间凿了一道沟,以示区隔。
扬雄又被委任一道重要任务,为王政君作诔文。这篇四字诔文虽然回忆了王政君的一生,实际上是颂扬王莽,因为王政君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博选大智”4,选中了王莽。
王政君的去世,使得王氏家族与刘氏汉家的最后一道羁绊也断绝了。这几十年,她尽享荣华高寿,几乎未吃过真正的苦头。她在汉元帝那里固然不得宠,但得到了尊重,所以终生爱着汉元帝,并在无尽的回忆里强化这种爱。比起当时的女性,她无疑是幸运的。
但她该不该为汉朝的覆灭负责?她是不是王莽的同谋?
很难给出直白的定论。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王政君长年居于皇室至尊地位,但极度缺乏决断力,她优柔寡断,总是延宕。她昔日面对董贤的果决,只因为董贤是一个早已确定的敌人和外人,而王莽是亲戚和同盟。面对王莽从安汉公到宰衡,到居摄,到假皇帝,到真皇帝,她本应从萌芽状态就知道这一连串的动作将会抵达何方,但她似是而非地拖延到最后一刻,直至不得不交出印玺。此后,她接受了新室的尊号,又深情追忆汉室,这未必是虚伪,而正是她缺乏决断力的表现。
归根到底,居于高位但毫无决断力,使她成为王莽最好的工具。
一个工具人,就不必苛责了,更不必诋毁她的性别。
她安葬之后,悲伤的皇帝称要服丧三年,预定的封禅之事暂缓,已经造好的封禅玉牒等礼器先存放在桂宫。
她安葬之后十年,新朝覆灭。
5.三摘尚自可
始建国五年,王政君去世不久,一则皇帝要迁都洛阳的消息,很快传遍长安。其实早在皇帝登基前,玄龙石上有符命在先:
定帝德,国洛阳。5
其实,新朝定都洛阳与其说是符命的要求,不如说是王莽的心愿。因为当时人们相信洛阳位于天下正中,而首都必须设在正中才正确。多年以后,刘秀拿着上面这六个字的符命,把都城设在了洛阳。
但当前,长安的居民对此颇为不安,居民们不想营造屋宅,甚至有人把自家都拆了。王莽很不高兴,下诏禁止毁坏首都,并透露了迁都洛阳的日期是“始建国八年”6。
这说明至少当下,始建国五年,王莽还没有改元的打算。
但到了十一月,天上突然出现彗星,二十多天后才消失。忧虑的王莽想起上一年夏天,有红云从东南方升起,弥漫天际;再上一年有蝗灾,还有从池阳县报上来的灾异,说是当地出现了许多小矮人的影子,身长一尺多,有的乘车马,有的步行,过了几天才消失。
当然,也想起了刚去世的王政君。
灾异给新朝的灿烂光辉蒙上阴影,王莽对“始建国”的年号发生了动摇。这个年号已经用了五年,按照汉朝的惯例,每五年或六年会定期改元,以示更始。王莽也想改元,但又舍不得“始建国传亿年”的信念。
根据这个信念,新朝将会存在万亿年,而且只有一个年号: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