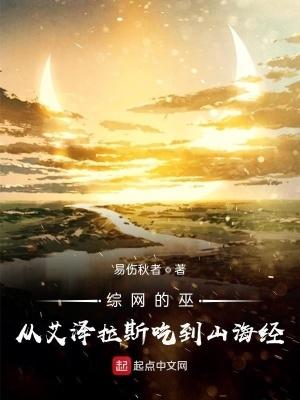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 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49章(第1页)
第49章(第1页)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9,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10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11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12。
“知当世之要务”,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3,这“儒宗”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14。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