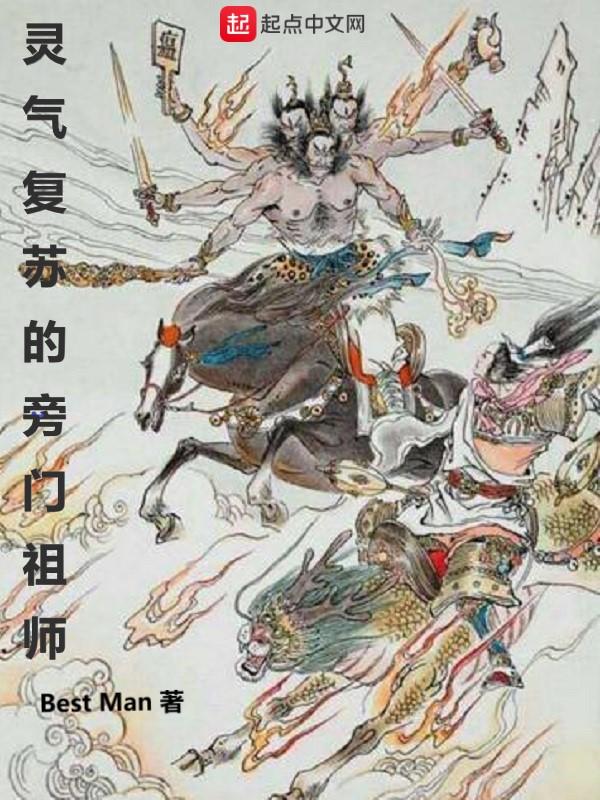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宴春台一双鲤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苏平芝刚要张嘴借此酸上一酸,见她还按着钱囊,极不甘心地憋回了喉咙。两人默默无言地坐在沿廊上,今日天清气朗,一丝云翳也不见。两个孩子帮老嬷嬷摘完了菜,蹲在树下和泥玩耍。他们舍不得弄脏衣裳,各将袖子攘在胳膊,却冻得小脸雪青。苏星回心里仿佛滴着冰。半晌她抬头,望着卷落的枯叶,眼神飘游到不知什么地方,“这些就是你给到我的消息了。没别的了?”苏平芝暗窥她的脸色,专挑她的软处继续刺,“爱恨切肤,除了他们两口子,你的眼里还容得下哪个。我这不是顺着往你心坎上说嘛。”这回苏星回难得的耐住了性子,“我是问裴彦麟。非要我说得如此直白是吗。”“那刚才我说的也没有不对的地方,是你不用心细究。我懒得多说,自己慢慢琢磨吧。”苏平芝起身要走,苏星回一个眼风扫过去。看见钱袋还捏在她手里,苏平芝又眼巴巴落下屁股,沉住气发表己见。“你想想,薛令徽,她在御前草诏掌文诰多年,是名副其实也当之无愧的第一女官。女主当政之年,外庭官员多和内禁宫官勾结谋私,宰相的任立多是宫官一句话的事。”他咧嘴一哂,“褚显真是什么缘由进去的根本不重要,而是她很可能和周策安联手,搞一出里外配合。这其中的利弊不容我再多说,你也该有警惕之心了吧,十九娘。”一口气说下来,有理有据,全然不见他平日的散漫。想到甘露元年一年间的滔天骇浪,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里原来都可能藏着勾心。苏星回自愧大意,但在只言片语里窥见弟弟内心的一角,又暗暗而笑,感到熨贴。“我的报酬值了吧。”他也知道捋顺了苏星回的毛。“还行。”钱袋到了手,苏平芝忙着塞进袖子,里头适时传来元氏的开饭声。苏星回唤过两个侄儿,“快洗好手,去吃饭。”元氏和老嬷嬷做了满满一桌的蒸素,孩子们抹得满嘴油星,年节里苏平芝也不吝惜几个钱,筛来好酒满上。姐弟俩在简陋的小院对酌,苏平芝敬她一杯酒,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厢吃过晡食,苏星回登车启程,赶在夜色前回到裴府。彼时天色大晚,她前脚进门,就有厮儿急忙过来禀告,“娘子离开后不久,吴王府里派人来请阿郎过府,至今未归。方才吴王府差人来送信,阿郎大抵后日才回。”苏星回说知道了,让他退下。回房脱去外裳,准备更换衣裳去书房,恍然一想不对。在烛火昏照下,她隐隐感到头沉心慌,高声唤来了兰楫。“阿郎有没有细说什么要事?为何要耽误到后日。”她问。家主行程下人哪能过问,兰楫自是不清楚的,打算去找来裴粤。苏星回却说不必麻烦了,她换上衣裳,在书房观看长子演练兵法。想是苏平芝的那几句话起了作用,这一整晚她心绪恍惚,胸口时而惊痛堵塞,就着这种困惑,半睡半醒熬到了天明。昨夜想了一夜,她终于想起一个可以问出实情的人,或许从那个人口中能探知细末。于是天一亮,她简单吃过朝食,将张媪和兰楫唤到跟前。兰楫一听她要出门几日,担心阿郎过问,她们会露出马脚。苏星回昨晚就做好了盘算,“我会把马车停在苏家做遮掩。阿郎若问,便说我许久不见家人,想多住几日,初五过后再回。”她打定主意要离京几日,兰楫不好继续挽留,和张媪打点一些细软就送她出门。清晨的苏家小院里,婢女云环撒粮喂着鸡鸭,元氏在搭的桌案旁教两个孩子读书识字。苏平芝枕手歪在床上,伴着幼儿的诵读,织布机年久失修的钱七声想着事,忽听到粼粼车声断在了门外。他一头爬起来,果不其然是苏星回来了。“哟嗬!”见她昨日才回,此时又来了,苏平芝准备呛她两声,一串丁零当啷的铜钱先滚进怀里。“去帮我租一匹马来。”苏星回回头吩咐厮儿把马车停放妥当。苏平芝看不明白她的意图,“你带着马,装什么疯。再说近年战事紧迫,马市大涨,我上哪给你租马。”苏星回斜眼看他,“你混迹市井,还要我教你办事。二十二,你就不想迁出这里,再回苏家去?你荒废了不要紧,别拖累弟妇和孩子跟你蜗居在此。”瞟到往这望来的妻子,再转眼看到两个年幼的孩子,苏平芝想到自己再不济,当时也是国子监太学的荫生。缘何到他这里,儿子只能念个不入流的书院。他一时给噎住,转身进屋,裹了件厚沉的袍子就出了门。半晌后回来,牵了匹杂毛瘦驹给她,“你上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