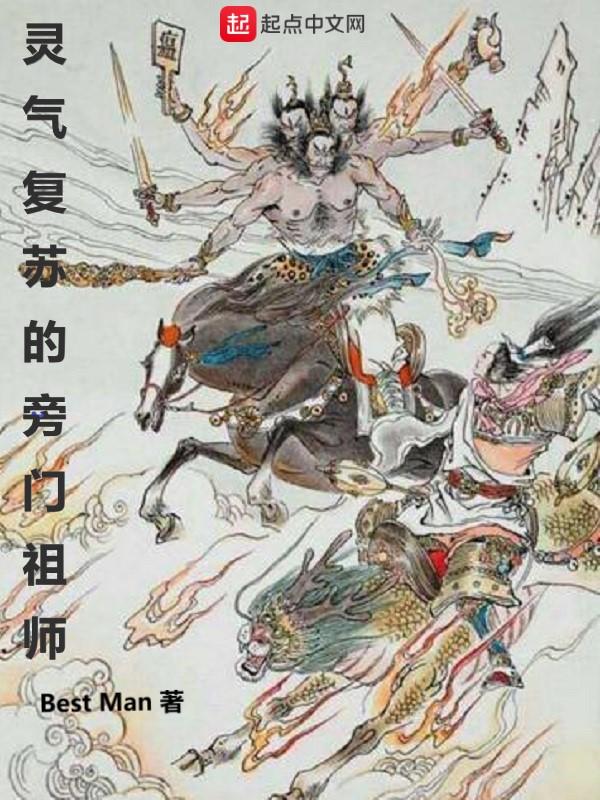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宴春台原文翻译 > 第94章(第1页)
第94章(第1页)
“不,我进了宫,他留在我身边毫无用武之地。”苏星回急得撑起上身,捧着他的脸哽咽道,“你带他走,我求求你,哪怕只是让他送信也可以。”她的心病始终悬在那,也悬在他心里。几次他都想不顾一切的抛开所有,和她厮守余生。甚至他尝试戒掉五石散,远离羽士。可没有办法,洪侃是圣人的眼线,他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第一时间传到圣人的耳里。“好。那你不要哭。”他吻过她的鼻尖,她的嘴唇,往她耳朵里呼着热气。苏星回破涕为笑,紧紧贴靠着他。裴彦麟吻干眼泪,“不会有事,我很快就回来。”“你担心我被支走,吴王禁足会遭不测。其实不用担心,这样的安排没什么不好。至少我很轻松。”他抚摸她的脖颈,玉色胜雪,灯下一片明曜。想到方才她欲言又止,似有肺腑之言。他几乎也想通了她的疑虑,俯向她的耳畔,“要我选那条路是不是?你没说出口,也是考虑到我不可以走,是吗?”“嗯。”苏星回热泪盈眶,紧拽他的衣襟,“我没有关系的。但我不要你成为众矢之的。”“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十九娘。你不能总为我伤神。”他道。苏星回反而更想哭了。“阿翁生平为天下计,我认为对的事,是侍奉福泽万民的明主。吴王若是关心民瘼,你就是为他肝脑涂地,我也不会有异议。但他畏缩不前,中庸软弱,实在难堪大任。我也明白,你扶持吴王,不过是更属意钜鹿郡王……可这条路太难走了。”难就难在裴彦麟出身世族,蒙受祖荫,裴家能把他送到如今的地位,也能让他粉身碎骨。裴家能者辈出,没有他还有另一个选择,他不可能能像圣人全力支持的周策安,可以心无旁骛地施展拳脚。“三郎,你让我如何是好……”裴彦麟安抚她良久,又沉思良久。直到暮色笼入中庭,烛火更为明亮。她的眼泪被吻干,唇也被堵上。苏星回舍不得虚掷光阴,安静地回应。绕在他身后的右手抚到肩后,指尖一笔一笔地划动。“在我背上旧时光整理,欢迎加入我们,历史小说上万部免费看。写了什么?”裴彦麟挨着她的嘴角,滚烫的手掌托在她瘦弱的背上。“你猜。”苏星回浑身酸软无力。“我猜是八个字。”裴彦麟贴向她的耳朵,只见苏星回点头。他咂摸了一番,又思忖了一时后,微哂道:“可行。”苏星回含泪点着头,再次用力撞在了他胸口。裴彦麟痛哼不已,她不管不顾,只和他亲密无间地相拥。…裴彦麟离开神都的第八日,石榴花初萌,延迟到三月的春闱放出皇榜,同月底,掖庭宫再进一批宫官。凤阙西门大开的当日,残阳照耀着洛水,广阔的宫道上近百架彩车鱼贯而驰,两岸的高楼飞阁站满了洒脱不羁的红男绿女。是豪俊游侠驻足,诗人高和截句,“三曲”教坊伎的调笑声。对那些去了高墙里的女子,外人总是充满无限遐思。十三岁掌制诰的御前红人薛令徽,平步青云的储显真都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而今又多了一个苏星回。从权臣发妻到和离求去,到温泉宫救驾,她的事迹甚嚣尘上,好坏参半,传遍了神都。苏星回在天津桥显听自己的名姓时,惊异到怕被人认出,而狼狈地乘车离去。她顾虑,私下问长子裴鹤年,“阿娘是不是笨,放着诰命不做,去做别人的家婢。”朝气蓬勃的少年道:“阿娘所行之路,即是光耀祖祢。”四月入夏,朝廷降诏,抚恤宫乱枉死的无辜,恩赏护驾的有功之臣。圣人以苏星回功不可没为由,另赐谕旨一道,特遣红衣中官架起一支规格极高的彩仗,在这日下午出宫宣诏。彼时已近黄昏,杏花飞谢,漫天的霞光铺在洛水水面。沿途的行人都亲眼所见,足有三十人的彩仗从凤阙驶出来。骈马驾起一辆仪舆,舆盖四角悬挂鎏金银香囊,车盖四沿遍缀着流苏羽毛,平稳地行驶在神都的坊道,撒下辚辚的车声。身穿绮罗,发戴钗环的宫娥手持障扇和珠伞。成对的红纱绢灯,成双的紫金云纹提炉成双,簇拥着华美的仪舆涌入这间逼仄简陋的小院。红衣中官手捧凤纸,向院子里跪迎的主仆宣读了圣意。中官读毕,收起册文。苏星回无视弟弟震惊的眼神,平静地跪谢了恩典。她自己又如何不震惊。想过百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盼来的谕旨会是一道册授。褒赠她为二品昭媛,赐仪舆入宫。另赐还邢国烈公的旧宅,以示浩荡皇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