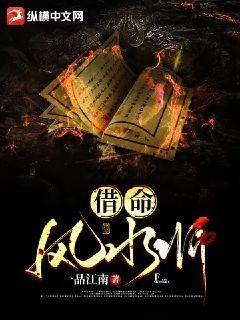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宴春台原文翻译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哦,是吴王在那?”周策安一阵沉默,嘴角却勾着笑,就仿佛看出了她的意图。苏星回讨厌他这种琢磨人心的眼神,笼袖就走。他忽然开口,“你出来时,其他两位殿下也陆续赶到主殿观赏歌舞。”最有可能的两位亲王她没有见到。那么谁会在明日发动宫变?身为女帝的亲子,帝位无可争议地会落在他们其中一人,其实不必铤而走险。暮色昏沉,春雨如酥,重新回到水榭,那些花木葱绿的叶片已泛着粼粼烛光,将两人身影也泅湿了。苏星回只顾朝前走着,周策安说了什么半她只听到梗概。无非是他当年的身不由己,事后又是如何悔不当初。他周策安一直是个爱重名声和颜面的人,过了十来年早就尘封的往事,他还在乎着那一时半刻的清白。苏星回想笑,都笑不出来。他当年来说这些话,她定然全信了。“你是心怀愧疚,还是后悔了?别忘了你是有妇之夫。你今夜要是和我断得比当初悔婚更利索,我还能高看你一眼。你现在这样藕断丝连,犹疑不决,做一副深情状给谁看!”苏星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自己低贱得像地上谁都能踩上一脚的烂泥。她拂袖就走,沓沓踩在甬道上,心绪不宁,竟都没瞧见对面行来了一群人。还是内侍喝道,她惶然回神,面前已然站了一位穿着广袖大衫的妇人。妇人高髻巍巍,插戴流光闪耀的金翅衔珠凤冠。她身后一众眼观鼻鼻观心的宫仆,簇拥着另外两个衣饰华美的女子。只是檐影落下,遮掩了两人的五官。只是一眼,苏星回就低下头让到一旁。她认得这个妇人,她是先帝之妹南平公主。南平公主十五岁下嫁给凉国公韦氏三子韦晃,婚后育有二子,但她不满丈夫无爵只是三品散官,求到先帝面前,要让自己的长子继承凉国公爵位。先帝不满韦氏气焰已久,非但没有理会她的哭诉,还寻由把韦晃贬到地方上做官。韦晃在外任苦熬了几年,圣人继位后才把他调回京。过了阵舒心日子,又逢今上打压关陇地区的势力。去年夏天圣人将他谪降了几阶,南平公主气得一年不肯入宫,让女帝很没颜面。她的近况不佳,连苏星回也有耳闻,不想今夜她竟肯露面。虽然还是眼高于顶,气焰不见收敛。南平公主走远了,苏星回才抬眼,后面两人跟着上来,吓了她一跳。她双眼无处躲闪,只得敛衽垂睫,“公主。”二十来岁的裕安公主挽着单刀半翻髻,插戴六支凤头钗,钗上嵌着天青色松石,在光下盈盈生辉,清冷夺目。而她的身边是锦衣玉带的褚显真。“苏十九娘。”裕安公主挽唇一笑,看了眼朝她行礼的周策安,从容提步。褚显真缀在身后,“殿下,容臣和苏十九娘说句话。”裕安公主不感意外,欣然道:“快去快回,阿娘等着你过去。”她又对一旁寂然不动的周策安道:“周相公不介意送我回宫吧。”她不给周策安任何拒绝的机会,抬步便走。周策安面容微怔,在苏星回和褚显真两人之间看了看,只能跟了去。廊上足音渐消,只剩两人,各据一处。雨水溅落衣裙,苏星回身上湿意更显。褚显真视而不见,秀眉轻挑道:“怎么到了这里?”苏星回还保持着奉迎的姿态,闻言她才伸直了背脊,和她并肩而行,“我现在是河内郡夫人的侄女。如果还不够,再加一个‘准许出入’如何?”她拿先帝的口谕来堵她的嘴,“随口一言你也当真了。”苏星回道:“君无戏言,你认为圣人说的是废话?”这可没人敢承认,褚不禁一笑,“你好像学聪明了。”她手挹霞裾,和苏星回一起站在了长廊尽头。台高足二十来尺,底下一丛桂树披挂着雨水,摇出一树婆娑。只是今夜格外不平静,桂树底下鞭笞声穿云裂石,响彻夜幕,刻意压抑的哭嚷仿佛幼兽的呜咽。灯笼摇摇晃晃,黯淡不明,也能见到跪在雨中的中官衣裳破烂,背上皮开肉绽,血殷一背。“再敢在御前嚼舌,我就亲手来拔你的舌头。”执刑的绿衣中官扔了藤鞭,疲累地甩甩腕子,和两三个内官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一路只闻那人气怒的叫嚣,从人却劝阻,“御前一时还少不得要他去,可别叫他死了。”“过了今晚再把他撵回内侍省,他不滚,我这身袍子就脱了给他敏良。”——甘露元年,裴彦麟死于宦官敏良之手。敏良?那个杀了裴彦麟的敏良?苏星回不由地向前走,脚下踩到边缘也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