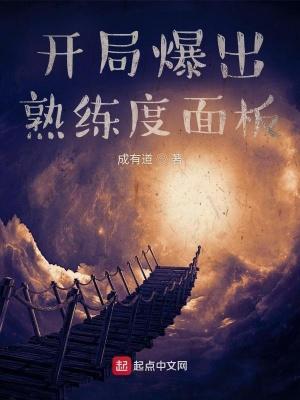秃鹫小说>困春莺温幸妤晋江文学城 > 14第14章(第1页)
14第14章(第1页)
nbsp;nbsp;nbsp;nbsp;屋内比外头稍微暖和些,祝无执解下氅衣,掀袍坐到窗边的木椅子上,扫视了一圈内里陈设。
nbsp;nbsp;nbsp;nbsp;窗沿上摆着个粗糙的陶罐,里头插着几只梅花。手边的木桌上放着针线筐,还有只做了一半的香囊。
nbsp;nbsp;nbsp;nbsp;地上摆着个炭盆,火星明灭,碳当是不太好的,隐隐约约透着烟气,也不太热。
nbsp;nbsp;nbsp;nbsp;他皱了皱眉。
nbsp;nbsp;nbsp;nbsp;天寒地冻,竟连好些的碳也舍不得买。
nbsp;nbsp;nbsp;nbsp;女人坐在炕沿上,手中的帕子搅成一团,时不时看他一眼,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
nbsp;nbsp;nbsp;nbsp;他没心情猜测她的心思,直接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nbsp;nbsp;nbsp;nbsp;“收拾收拾,随我去朝邑镇。”
nbsp;nbsp;nbsp;nbsp;温幸妤愕然抬眼:“去朝邑县?”
nbsp;nbsp;nbsp;nbsp;祝无执嗯了一声,补充道:“该拿的拿好,日后不回这里。”
nbsp;nbsp;nbsp;nbsp;温幸妤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这里,她悄悄瞧了眼祝无执,心里有很多话要问,譬如为何忽然来接她。
nbsp;nbsp;nbsp;nbsp;她不是聪明人,却也有积年累月做婢女练出来的敏锐。旋即反应过来,祝无执肯定是有事需要她,才会带她走。
nbsp;nbsp;nbsp;nbsp;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她站起身,给祝无执倒了杯热茶,就起身收拾行李去了。
nbsp;nbsp;nbsp;nbsp;明明生活的日子不长,但东西却不少,整整收拾了三箱子,才算是装完。
nbsp;nbsp;nbsp;nbsp;像是鸡鸭一类的活物,她有心拿,可祝无执显然不会让她带这些东西。只好依依不舍把养了几个月的鸡鸭,折价卖给了隔壁婶子。
nbsp;nbsp;nbsp;nbsp;地窖里的菜,她装了一麻袋,剩下的都送给了邻居,权当是感谢她们这段时日的照顾。
nbsp;nbsp;nbsp;nbsp;等全部收拾好,车夫帮忙搬到了车上。
nbsp;nbsp;nbsp;nbsp;温幸妤掺了一铜盆温水,将手上、脸上的灰洗干净,才推门回了厢房。
nbsp;nbsp;nbsp;nbsp;青年临窗端坐,眉眼神色淡淡的,叫人看不清喜怒。
nbsp;nbsp;nbsp;nbsp;温幸妤的目光落在桌上,停顿了一下,而后静默垂眼。
nbsp;nbsp;nbsp;nbsp;木桌上的陶杯中,碧绿的茶汤依旧是满的,平静地倒映出青年冷漠的面容。就连杯子的位置都未换过。
nbsp;nbsp;nbsp;nbsp;她又看了眼祝无执,才后知后觉发现,他身上的衣料,已经不是半个多月前的棉布了,而是柔滑细腻的锦缎。
nbsp;nbsp;nbsp;nbsp;视线转到木架上的白色大氅,细细看了两眼,她方意识到那并不是不值钱的杂毛氅衣,而是昂贵的狐毛大氅。
nbsp;nbsp;nbsp;nbsp;仅仅半个多月,他就已经摆脱了窘迫清贫,再次与她成天壤之别。
nbsp;nbsp;nbsp;nbsp;这样的人,不愿意喝苦涩的粗茶实属正常。
nbsp;nbsp;nbsp;nbsp;她沉默了一会,收敛好情绪,开口道:“收拾好了。”
nbsp;nbsp;nbsp;nbsp;祝无执正在思索陈文远的事,被打断后,微微皱眉,瞥了眼温幸妤。
nbsp;nbsp;nbsp;nbsp;见她垂目敛容,一派温顺的立在炕边,淡淡嗯了一声,而后起身披氅衣,率先出门。
nbsp;nbsp;nbsp;nbsp;温幸妤把炭盆熄了,将几个房门都落了锁,才朝院门外走。
nbsp;nbsp;nbsp;nbsp;阖院门时,她透过半闭的门缝,再次看了眼这个生活了几个月的小院。
nbsp;nbsp;nbsp;nbsp;日光浅淡,一阵冷风刮过,吹落桂花树枝头堆积的白雪,簌簌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