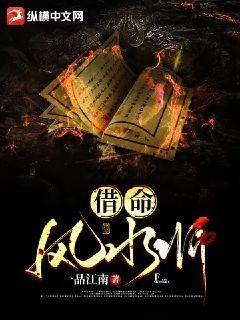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必齐之姜讲的什么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这岁暮季节虽然令人讨厌,但这几个月里有诸儿相伴,我倒希望春天永远也不要来了。夭桃三月初三如期而至。暖风细雨,触手生春,一夕之间,便是莺歌燕舞,柳绿花红。天气逐渐回暖,夜里睡觉的时候我已无需借助诸儿的体温。但还是仰赖他春风拂面的气息,上瘾似的,片刻不能离开。今天是我的生辰,也是半夏在家过的最后一个女儿节。再过几天,她就要去卫国和世子姬急成嘉礼了。我的一生经历的离别太多,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让果儿去疾医那里讨了些白芷,又去园子里采了些初放的桃花,浸了五坛子桃花白芷酒,埋在母亲堂前的五株桃下。这方子是卷医书上抄来的,外敷内服,养颜驻色。我年纪尚小,还用不着它,只是诸儿爱喝。他说这酒喝了齿颊生香,嘴里像含了朵桃花似的。我偷喝过一回,开盖的时候确有花香袭人,但吃起来并没有他说得那般美味,倒是辣得够呛,也断了我日后喝酒的念头。别处的桃树都开花了,就这五株桃任性,每年都迟放。我拿着犁头在每棵树下刨出一个坑来,分别埋上一坛封好的酒。什么事都有人代劳,就这件事我非得亲历亲为,已经作下了习惯。忙了大半晌,回去的时候路过园子,半夏正领着芙蓉在河畔流杯祈福。近来我很少去半夏那里滋事,有时候路过她的宫,才抬脚要进去,又不知道进去以后要说些什么,便作罢了。想来已经很久没见着她了,日后也不见得有再见的机会,离别在即,反倒念起她的好来。半夏求得很虔诚,她心里想要什么,不必说出来我也知道。我向来不屑她所求所想的,但她若觉得好,那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吧。我走近她,从芙蓉的托盘里捻起一只玉觞,里面盛着一些醴酒,撒了三两瓣桃花。沿着河岸已有不少流杯祈福的女眷宫娥,水里浮满了各色盛花盛酒的杯子,密如天上的繁星。女儿节年年如是,也不知其中几个是心想事成的。每每见到这番景象,都让我想起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话来。我学着她们的样子将流杯托放进水里,合十双手,静默祷祝。样子虽学得好,可心同止水,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求,只眼巴巴看着盛酒的玉杯随波逐流,漂到我目不能及的地方,化为乌有。我估摸着它的去处,许是顺着这汪春水漂到宫墙外头去了,那倒是个极好的去处。半夏见我求了半天,好奇问道:“妹妹求的什么?这么出神。”我笑道:“民有谚:三月三,生轩辕。今天是个求嗣的好日子,姐姐就要出嫁,自然是为姐姐求的。姐姐嫁的世子,日后定成国君;姐姐生的孩子,日后也会成为国君。”这些话倒不是我平白想出来的。前一阵子和小白溜出宫去玩耍,见一个鹑衣百结的乞丐,我见他可怜便给了他几个钱。他说自己是个占卦的相士,既收了我的钱便要为我卜上一卦。我哂笑,“你既算得准,就该算算你自己,又何以落魄至此?”他嘿嘿笑了两声,堆了一脸褶子,道:“这些都是命里定下的,我虽能窥得一二,却无力回天。人啊,就只能顺命而为。你家祖先就很懂这个道理,发迹的时候不到,再怎样殚精竭力也是没有用的,不如找处好风好水,安心垂钓,钓到鸡皮鹤发,自有负命者上钩。”“先生倒连我家祖先都算出来了。但,你既无法改变,我也不想知道。”我想拉着小白走,他却不肯走了。小白就是个好奇心极重的人,“先生既算得准,知道也无妨嘛。”那老头又是嘿嘿两声,褶子里都要挤出油来了。他席地摆了卦摊,撒了一把蓍草组成个卦象,道:“你们兄弟四人,姊妹两人,可是?”我用袖子掩着鼻,遮住些他身上的酸臭,退了几步,不耐道:“你既知道我们是谁,这还用你算,天下人都知道了。”“莫急嘛,我还没有说完呢。照这卦象,你们兄弟四人同命,姊妹二人同命。”“如何同命法?”小白兴趣盎然。“一枝半夏,一朵舜华,共生共荣,你们姊妹二人都是极显赫的命呢。父亲是一国之君,兄弟是一国之君,丈夫是一国之君,儿子是一国之君……”算卦的说得摇头晃脑、抑扬顿挫。说到得意处,却被我打断:“我们与邻国世子早有婚约,尽人皆知,这卦换谁都会算。”“可你们谁也嫁不成。”算卦的抬脸看我,露出狡黠的笑。我只当他故意气我,拉着小白欲走。小白却愈发兴致,蹲在地上不肯走,追问道:“那兄弟们的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