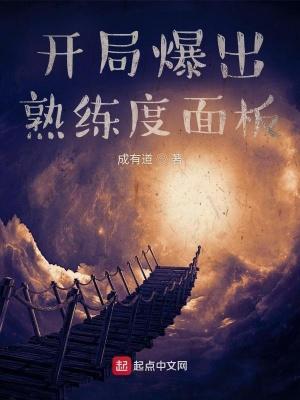秃鹫小说>爱欲焚身 > 第18章(第2页)
第18章(第2页)
原楚聿比所有人都要先回到房间,湿透的衣服黏在身上,外面吸了水的浴袍沉沉地坠在身上,格外不舒服。
可是更不舒服的另有其他。
林琅意见他咳嗽得厉害,还想游过来扶他,被他反应极大地避开了。
他并不得体,耻于出口的那一面并不想要让她瞧见,他很坚决地转过身背对着她,并且很快要来了衣服和浴巾离开了。
但是回到房间,密闭的私人空间却将掩耳盗铃的事实再次放大。
这是与她一墙之隔的本该属于程砚靳的、她的未婚夫的房间,于是根本消不下去的燥意烧的更旺。
确实是程砚靳的房间,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房间是他在住。
鸠占鹊巢?
道德败坏?
他冷静地对着镜子看了下自己泛红的脸,耳垂处烧得更红,连眼睑那一圈都分外明显。
原楚聿在浴室里简单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将花洒的水拧小,退了两步微微弓着背倚在瓷砖上,整个后脑勺都紧紧地贴在上面,微仰起脸,喉结有些不耐地上下滑动了几次。
大腿上被她的指甲刮擦出来的痕迹还没消退,因为他方才淋浴的水温太高,还类似过敏一般在皮肤上浮得更明显。
原楚聿漫不经心地用手指在那些凸起的划痕上摩挲了几下,闭了下眼,更用力地用指甲掐下去,留住她的痕迹。
暴力和忄生都有一种濒临极限的疯狂,肾上腺素和他的心脏频次一样急促上升,他甚至能听见汹涌情氵朝时自己的耳膜都在鼓鼓撞击。
隔壁传来隐约的水声,是林琅意回来了。
比预想的要晚,她吃到荔枝慕斯了吗?
喜欢吗?
原楚聿的眼皮上绯色更甚,他甚至伸手将花洒彻底关闭,最后两三滴花洒水滴滴落在地面的声音被隔壁涓涓的水流盖过,浴室里只剩下他的喘息声。
他就这样垂着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抚慰,另一只手却从台面上取过自己的手机,点进贝母头像,断断续续地思索自己该如何邀请她来自己的房间详谈。
他单手打了几个字,手指上没有擦干的水渍和雾气让屏幕变得不怎么灵敏,短短的一句话打得滞涩缓慢。
他用手背蹭了下下巴被她阴差阳错亲吻的地方,光是碰到那块皮肤都让他无可救药地想起水下宿命般的一切,他停顿许久,再垂着眼继续打字。
对着一个贝母头像做这种事并不比对着她的身体做这种事要高尚,只会让他认清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斯文败类。
隔壁停了水,吹风机的响声轰轰,原楚聿平了平呼吸,这才重新打开花洒,浴室里再次慢慢腾起热气。
“抱歉,我是不是来太早了,打扰到你洗漱了?”她看到他还潮湿的头发,有些抱歉。
“没有。”他的嗓音还有些哑,冲她绽开一个毫无破绽的笑容,“刚刚好,请进。”
原楚聿觉得自己与林琅意谈得非常顺利,谈判和交涉是他擅长的领域,一点点放出诱饵,再让她交换一些无足轻重的代价,比如与程氏的联姻到此结束。
他今日得到的甜头太多,与她同在一屋促膝交谈的距离也让他昏了头,他将一切都想的太好太顺利了,以至于林琅意毫不犹豫地起身为程砚靳开门,并牵着他的手双双站在自己面前时,他连客套礼貌的表面笑容都维持不住了。
“程林两家将要联姻的消息广而告之了。”
原楚聿的目光定定地停在他们十指相扣的手上。
那是林琅意主动牵起的,这一点让他更加嫉妒、挫败和难过。
早早散布消息,可以让那些揣摩公司前景的投资者闻风而动,从而拉起股价,确实是应山湖现在能柳暗花明的一步。原楚聿对于这种生意场上的策略太熟悉不过,所以他能说出一万个理由来赞同这一步棋。
程砚靳的反应也相当耐人寻味,原楚聿第一次见到他表现出这样浓浓的护食意味,把林琅意藏在背后,甚至还拉着人远离了自己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