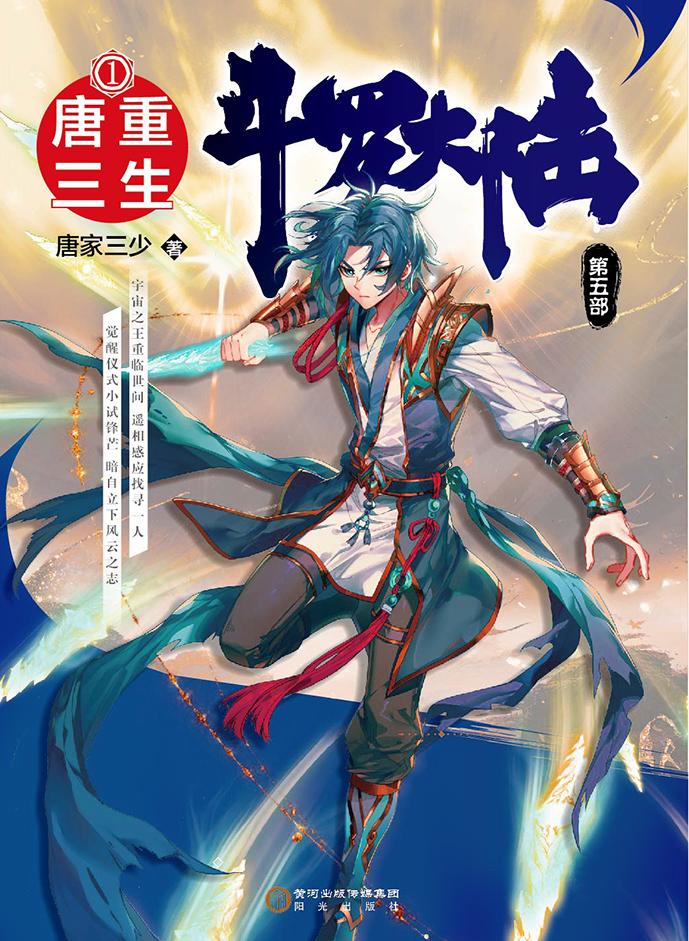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此案无头又无尾 (打一字)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阿月先是一怔,随即猛地瞪大眼睛,语气里透着几分兴奋:「影人戏?就是时下最时兴的那种?可这宅子不是很早之前的宅子吗,怎么会有这种戏台?」
她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伸手在绢布后轻轻拨弄了一下,眼里满是新奇。
李长曳却没有立刻答话,只是静静地望着戏台,目光深沉,像是在思索什么。片刻后,她才开口道:「影人戏虽是近些年才流传开来,最早却并非民间戏法,而是只在宫中或权贵之间传演,寻常百姓,甚至寻常士族都难得一见。」
阿月若有所思地嘀咕道:「那这宅子的主人,难不成跟宫里有什么关系?」
她的话音还未落,忽然听到赵霆在戏台后方喊了一声:「你们快来!」
李长曳与陶勉对视一眼,立刻朝后台走去。
戏台后方空间极其狭窄,仅容两三人并肩而行,四周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赵霆半蹲在角落里,手边放着一个看上去已有些年头的旧木盒,盒盖微微掀起,露出几张泛黄的牛皮影人。
李长曳蹲下身,伸手打开盒盖,目光微微一凝。
盒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几张用牛皮制成的影人,其中一张影人赫然穿着本朝官服,袖口和衣摆处的纹饰仍依稀可辨,手中握着一把沾染着红色痕迹的大刀。而另一张影人则是一名身着短褂的女子,衣饰简陋,姿态僵硬。她的短褂之上,同样布满了斑驳的红色痕迹。
赵霆凑上前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这像极了那身着官服之人手持大刀,砍死这女子的杀人戏份!」
他说着,下意识地后退半步,眼神有些发直。
李长曳沉吟片刻,伸手取出那两张半人高的影人,缓缓贴在方才挂起来的绢布后。赵霆见状,也在后方点燃了一根蜡烛。
微弱的烛火映照之下,绢布前方的影像渐渐显现出来。只见那官服人影高举大刀,短褂女子则仰面倒地,姿态僵直,像是被当场斩杀。夜风微微拂过,影人随风晃动,仿佛整个画面都活了过来。
戏台前,影子清晰可见,仿佛有意让所有人都看到这场残杀的故事。
几人看到这一幕都屏息凝视,没有一个人出声。
不知过了多久,李长曳终于打破沉默,语气低缓:「我想,孙巡检和余先生便是在铜镜中看到了这一幕吧。」
阿月皱着眉,目光在影人投下的剪影间来回打转,似是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可如果他们看到的都是同一幕,为何余先生疯了,而孙巡检却自尽了?」
李长曳盯着绢布上的影像,沉吟片刻道:「或许,这一幕戏,与他们有关。」
说罢,李长曳没有再多做解释,转身便朝堂屋走去,步伐果断利落,仿佛心中已有答案。她边走边道:「要想知道孙巡检为何自尽,便必须先查清楚——这座宅子的主人是谁。」
一行人随即跟上,穿过昏暗的院落,回到堂屋之中。
堂屋内,陈设依旧沉寂如旧,烛火的微光在木制窗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依然残留着一丝尘土的味道。
然而,这里没有一件物品能直接指向房屋主人,连一个能证明身份的字迹都不曾留下,仿佛这里的主人只是个影子,从未真正存在过。
李长曳微微皱眉,她将目光放回那铜镜之上,手指在铜镜的背面缓缓拂过,忽然触碰到一处微微凹陷。她心头一动,手指顺着那处凹陷轻轻划过,才察觉到那竟是一道极浅的刻痕。
她眸光一凛,立刻道:「赵霆,把这铜镜翻过来。」
赵霆闻言,抬了抬眉,一脸无可奈何:「李典史,这镜子可是和桌子连在一起的。」
「力气别白长。」陶勉见状补充道,语气平静,语气却完全不容拒绝。
赵霆没有办法,只能撩起袖子,咬了咬牙,单手按住桌角,另一手稳稳抓住铜镜边缘,用力一转。桌脚在地上摩擦出一丝闷响,铜镜缓缓转了过来,沉甸甸的后背映入眼帘。
只见铜镜背后,雕着四个大字:
宜室宜家
字迹因岁月侵蚀略显模糊。再往下,隐约可见一行小字:
姚府所制
阿月轻轻倒吸一口气,小声嘀咕:「宜室宜家,这不是嫁妆上才会刻的吗?这难道是个陪嫁用的铜镜?」
李长曳抬起头,眸光在昏暗的堂屋中缓缓扫过,似乎是在将所有的线索快速拼凑起来,继而缓缓道:「这些年来,可有哪个姚姓人家显赫一时,又与这刘家庄有姻亲关系?」
一旁的陶勉听到这话,若有所思:「姚家?若要说这姓姚的,还能称得上『达官显贵』的,那可就只有十几年前的姚丞相了。」
他语调平稳,尾音微微拖长,却带着几分耐人寻味的意味。
赵霆闻言,不由皱眉:「姚丞相?可他……」
陶勉眼神微微一沉,接着道:「可他早在十几年前便被判了流放。传闻他一路凄惨,未到流放地,便遭山贼劫杀,全家上下,无一幸免。」
李长曳接着道:「那可曾听闻姚家是否有女儿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