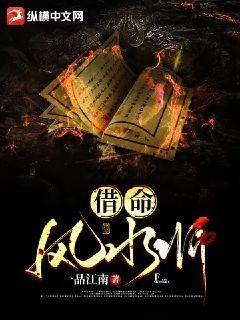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暮光之城里凯厄斯 > Column 73(第3页)
Column 73(第3页)
“你骗我。”我听到自己瑟瑟发抖的声音。
不是说追上他就算赢了吗,可他为什么要往下跳,那可是悬崖,一不小心就会摔到粉身碎骨的悬崖。
而且我到底为什么要跟着他跳下来,他又不是一沓钞票,四散在空气里没人去抓。
身体一个劲往里缩,双手凭感觉紧揪住两片衣领,用力到指节突起几乎爆出的地步。洁白的衣领也被我揪出不雅的皱痕。可关心他人是种很高尚的情感,而现在自顾不暇的处境让我压根没法让这种高尚留存在心里。
看到那些皱痕,不仅没有放手的打算,反而绞尽脑汁思索怎样才能抓得更紧,不至于掉下去摔个粉身碎骨。
当然,我也希望自己无所畏惧,傲骨铮铮,能指着凯厄斯的鼻子破口大骂,指责他为什么要让我们都陷入这样危险的困境。可是恐高的老毛病出现得实在不合时宜。
恐惧筛掉大脑里多余的情绪,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产生不了任何似是而非的想法,大脑里唯一还算清晰的念头就是往里缩,然后拼命抓紧。
“我可没让你跳下来。”他也不知道在嘟囔什么,都这种时候还有那么多话可说,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轻轻的笑声从背后传来,所以这到底有什么可得意的,得意我们不知道哪一秒就双双坠海然后被鲨鱼吧唧一口的宿命吗?
难道活太久真的会活腻吗?
“我们……”我们怎么上去啊,你能想到跳下来就应该能想到上去的办法吧?别告诉我你的办法就是打电话给消防队,我无比确定再好心的人类也不会来救吸血鬼。
“凯伦,睁开眼睛。”他不笑了,声音里突然多了几分严肃。箍住我的手臂松了松,后背被人猛然一推,腰部重新传来挤压感,一口气还没喘完,双脚二度离的惊悚就令我倒吸入几口咸涩的凉气。
绝不。我紧紧闭着眼,恨不得能从空气里摸出把订书机将眼皮严丝合缝订起来。这太可怕了。
“睁开眼睛。”命令变成了威胁,生命就像悬在摇摇欲坠的钢丝上,每一次呼吸都艰难的可贵。
当然当然,按道理讲,从这里掉下去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危险。吸血鬼的防暴能力太强大了,强大到我都想顶礼膜拜。所以我顶多摔个四分五裂,再被涨落的潮汐冲上海滩,慢慢复原就是了。
但问题在于,光是想想自己现在处在什么高度就让我毛骨悚然,生不如死。更别提想象从这里掉下去,而且还是被人推着掉下去。
这看起来可不像是蹦极或者跳伞。
“你到底……”你到底想怎样。我哆哆嗦嗦,连把一句话完整说完都做不到。
感官全部集中到脚,我能感受到大洋上空混乱的涡流变成海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的强度,感受海浪每一次高高抬起又重重拍下的力度,感受海水缓慢蒸发濡湿空气改变的温度。
这些都是很壮美雄奇的场景,是普通人千金难求的观感,可问题在于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自然,现在只让我感到害怕与惊恐。
抱着我的手臂又松了松,眼看就要把我扔下去。我真是佩服凯厄斯想一出是一出的脑回路,他这种说一不二唯我独尊的性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而我刚才,到底为什么要为了抓住这么一个家伙而跳下来。
迫不得已,我颤颤巍巍将眼皮掀开一条缝,刚眯到点光,又赶忙合上,合上不到半秒,便强迫自己再次睁开。
漆蓝海岸和灰白沙滩,在眼里统统变成了无生气的青灰,泛滥着阴暗的光泽。晚间开始有雾,从海的深处涌上岸,缭绕出触手,绞杀一切。
长时间双脚悬空让大脑有些微微眩晕,我都不确定自己说出的到底时几个凌乱无序的单词,还是正常完整的话。
“我……我睁开了。”麻烦你快点把我放下来吧,不论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现在都已经达到了,所以请不要再戏弄我了,再不停手我真的要掉下去了。
“那就站稳了。”双脚最先接触到的不是粗糙地面,而是某种质感细腻光滑的东西。箍住我的手换了个姿势,改为抓住肩膀。
我不知道用掉多少勇气低头飞快往下瞥一眼,只捕捉到一双黑色鞋面在薄雾里影绰。
看起来是款式很熟悉的鞋子,就是比我的那双大了点。
我用力闭下眼,然后想起什么似的赶忙睁开,仿佛有人举着火把要烧我的眼皮,反正这感觉也差不多。
我是多么想不管不顾用力一跺脚,最好是能踩到他双脚骨折,以此好好报复一下身后这个任性妄为的家伙。但现在这样的处境,显然不能包容我这么恶毒的想法。
“我们到底怎么……怎么下去。”他的心血来潮总不该是角色扮演岩石雕像,在这里站上个几百年任由海水侵蚀和秃鹫啄食吧?我可没有那么伟大的精神成为当代普罗米修斯。再说吸血鬼不是惧怕火焰?我不觉得偷盗火种对我和他任何一个有什么好处。
悬崖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谈话声,铝制易拉罐被捏扁的抽气声,以及诸如石子般的重物跌破海面的噗通声(多么庆幸那不是我!尽管照这情况看来或许不久后就是了!)可以预见的是不远处就有人类,而且很多。
他们大概是来这里旅游观赏风景。是的!是的!完全能够理解——悬崖绝壁,落日美景,沙滩排球,临海烧烤。
光是说说就让人心生向往,再有滤镜和精修的加持印刷在旅游手册上,真是想不欣然前往都难。在他们眼里,这个悬崖绝非夺命之谷,而是自然奇迹。
“只要你想,我们随时都可以下去。但下去之前。”有什么东西撬开紧握的拳头,贴上掌心。我完全没有任何质疑或反抗的心情,心里只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你得先做完这个。”
视线下移,手指蜷缩,我感受到的同时看清被强塞进我手里的东西:一个长方形状物体,有着金属外壳和磨圆棱角。
那么熟悉。
“扔了它。”他凑在我耳边,海风洗净那声音里惯常的暴躁与命令,甚至洗去那些要把我扔下去的威胁与逼迫。
留下的只是一个二十岁青年的声音,一个略带波澜的声音,一个清晰到近乎请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