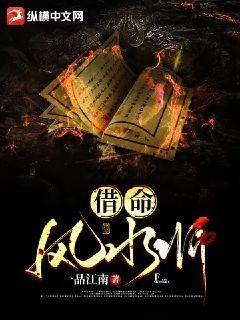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候门恶女又开始得宠 > 第103章 这份情本将记下了(第1页)
第103章 这份情本将记下了(第1页)
此刻,主帐内,楚逸尘着一袭玄色锦袍,稳稳坐在上座。
他嘴角噙着那抹看似温和的笑意,修长手指轻轻拂过案几上的茶盏边沿,悠悠开口:“贾都督,此次本将外出军练,多亏你坐镇军中,稳定军心,楚某感激不尽。”
听着他低沉醇厚的声音,贾仁贵忙不迭站起身来,双手抱拳,身子微微颤抖,连声道:“楚将军,您这可是言重了。不过是卑职应尽的分内之事罢了。将军在外浴血奋战、奋勇杀敌,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卑职所做的,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何足挂齿,何足挂齿啊。”
赵副将立于一旁,将腰杆笔直如松,铁甲森然,目光锐利地盯着面前的贾仁贵,仿佛要在他身上盯出个窟窿来。
楚逸尘指尖有节奏地轻叩案几,声音温润却透着冷意,仿若一把软刀子:“这份情,本将记下了。”
贾仁贵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紫袍下的手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袖,他干笑两声,声音发虚:“楚将军言重了……下官、下官不过是奉命行事……”
他此刻肠子都悔青了——本以为楚逸尘身死深潭,自己这个兵部侍郎好不容易钻营到中军都督府右都督的位置,正盘算着如何在军中培植亲信,哪曾想这位“已故”的主将竟突然活着回来了!
楚逸尘慢条斯理地端起茶盏,氤氲热气模糊了他眼底的锋芒:“贾都督似乎……很热?”
“啊?啊……”贾仁贵慌忙用袖子擦汗,“近日天……天气反常……”
一旁的赵副将突然冷笑一声:“末将倒觉得,今日格外凉爽。”
帐内空气骤然凝固。
贾仁贵如坐针毡,后背的官服早已被冷汗浸透,他偷眼看向楚逸尘,却见对方正悠然品茶。
“贾都督为何不喝?”楚逸尘用下巴点了点案边的青瓷茶盏,“都督此次而来,正巧本将出京在外,未能亲迎,实在失礼。军中粗陋,还望都督莫要嫌弃,好在本将营中正巧也有这武夷岩茶,听闻都督在兵部时,最爱此中韵味。”
贾仁贵官袍下的膝盖一颤,连忙端起杯盏,捧茶的手晃出半圈涟漪:“谢过将军……楚将军竟记得下官这点喜好,下官实在荣幸之至。”喉结滚动咽下的不知是茶还是惊惶。
楚逸尘素来极少上朝,就算进了宫,大多都是陛下亲自召见,也鲜少与兵部之人闲叙。
何况自己也是沾了萧国舅的光,才新任兵部侍郎一职不久,与楚逸尘打的交道可谓少之又少,没想到,他竟连自己喜好喝什么茶都知晓,贾仁贵不免觉得后背发凉。
楚逸尘放下茶盏,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却仍笑着说道:“贾都督过谦了,听闻你在兵部时便对军中事务多有建言,此番亲临军中,定是带来了不少新的见解吧。”
贾仁贵心中一紧,他深知楚逸尘在军中威望极高,自己贸然插手军中事务,本就引得诸多不满,此刻被楚逸尘这般一问,更是慌乱,结结巴巴地回道:“楚将军,下官……下官初来乍到,对军中诸事还不甚熟悉,一切自然是以将军的决策为主,下官定当全力辅佐将军。”
一直沉默站在一旁的赵副将,此时微微皱眉,目光在楚逸尘和贾仁贵之间来回游移,忍不住开口:“贾都督,既然来了军中,往后诸多事务还需您多费心。只是军中将士们向来只认能带领他们打胜仗的将领,往后行事,还望都督能顾全大局。”他的语气不卑不亢,话里话外却带着对贾仁贵的警告之意。
贾仁贵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干笑两声,点头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赵副将所言极是。”
“坐。”楚逸尘执壶斟茶,荡漾的茶汤映着他似笑非笑的眉眼,“贾都督何须如此拘谨,既然来了,不妨把营中当作自己家。”说着,指尖还在说到“家”字时轻轻顿了一顿。
“哐当——”
贾仁贵刚坐下的屁股,又猛地从太师椅上弹起来,紫袍差点带翻了茶盏。
他几乎是扑到楚逸尘案前:“将军折煞下官!这中军都督职原就该……”
“贾都督这是做什么?”楚逸尘抬手虚扶,玄色广袖却始终离他三寸,“兵部文书墨迹未干,莫非……”他突然倾身,冷松香扑面而来,“贾都督是要抗旨?”
贾仁贵膝盖一软,险些跪下去,冷汗顺着鬓角滑下,喉结滚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楚逸尘不再看他,转而望向赵副将:“本将不在这些时日,军中如何?”
赵副将抱拳,声音洪亮:“回主将!得知您遭山匪劫杀,军中无人相信!弟兄们都说,将军战无不胜,岂会折在区区山匪手中?”他顿了顿,声音清冷道,“只有张校尉伤心欲绝,当夜便在营帐中……上吊而亡。”
楚逸尘指尖一顿,茶盏轻晃,竟显出几分“动容”:“哦?莫不是他为本将殉情而死?”他叹息一声,摇头道,“实在感人肺腑。赵副将,务必好好照拂张校尉家人。”
说到“家人”二字时,他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贾仁贵,指尖在案几上轻轻一叩,声音不轻不重,却震得贾仁贵浑身一颤。
贾仁贵慌忙接话:“是……是啊!张校尉对将军情深义重,实在令人……令人敬佩!”
楚逸尘垂眸,似在回忆:“从前张校尉只是军报没有摆放整齐,本将便罚他顶着水桶扎了两个时辰马步。”他抬眸,眼底寒光隐现,“现在想来,是否太过严苛?”
贾仁贵咽了咽唾沫,冷汗已浸透内衫:“楚将军治军严明,张校尉想必……心服口服……”
楚逸尘忽然笑了,眸色温度让人辨不出喜怒:“是吗?”
他缓缓起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刚刚新官上任的贾仁贵,嗓音低沉:“那贾都督觉得……本将是否真如京中之人所称的冷面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