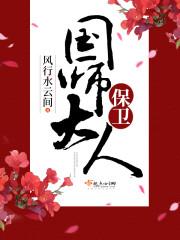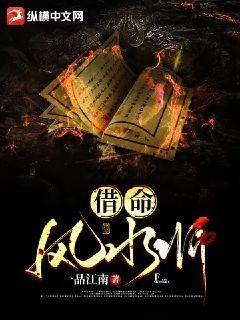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巧媳当家 > 第十八章(第5页)
第十八章(第5页)
市面上开始有回鹘装出现,果真华美如张贴画所言,有钱的跟着潮流,没钱的捎带些其他小玩意儿。
那大食国之帽也甚是奇特,价钱也低廉不少,又仍能赶时兴,因此卖得也好。
逐渐的,人们发现,这巧娘子店里的服饰甚是奇特,俱是乘了朝贺之风的,想要哪国之扮,只管去看。
当然,数量多少,价钱高低,可要自己忖度。
别家衣肆后悔呀,眼红呀,可日赶夜赶也只做出十几件,哪来这么多存货?
巧娘子啊,果真是巧思连连。
如此之风,她究竟是如何想到的?
其他售卖酒器的,金银宝石的也不甘示弱。
乘了此股东风覆盖了酒楼的张贴画,又变成一张张更为夸大的宣传图。
值此之际,那张贴画已淡下去许多,人们都等着,那来贺之日,亲眼见见那盛景!
二十日,十日,五日。
明日。
这月,薛枝与巧文俱很忙。
两人仍宿在离寺院两条街的宅子里,日出两人起来,点头而过,薛枝牵了马出行,巧文跟上。
却被让开。
“应酬之事繁多,不适于你。”
“我走了。”
巧文还想说些什么,薛枝眼一撇,离去了。
有时这般对话多了,他会问,很好奇。
“怎么,四郎与你那筹备之事如何了?他怎么不来了?”
“他去选去比剑了,衣裳那事早都定了。”
“其余也不是我们能管得了。”
“嗯。”
一句简单的知晓。
巧文仍看着他离开。
叶黄调落,掉在远走之人身后,一片片,渐渐遮住了那道人影。
衣肆如今正是火热,一应人情极多。
但出门的只一人,晚归的只一人。
有些夜很深,他才回来,带着醉意,有时什么也不带,但常常,桌上会出现一纸一纸账页,和许多散落的铜钱。
于是,另一人便知道了,这衣肆在这满地势力场上仍蒸蒸日上。
甚至蓬勃发展着,在外,各大同行谁不知巧娘子家那个郎君,如虎如狼,入了商会,谈判,分利,一应算计,正如几十年前的薛家,一夜之间如竹笋般破土而出,势不可挡,团结势力,抓住一切机会,往上爬,往上追。
于是,巧文在短短一月之内,有了三张地契——
自此,南北两市,西京长安两市各存了巧娘子名号。
曾经口中的分店,竟如此轻易般,半秋之间,林立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