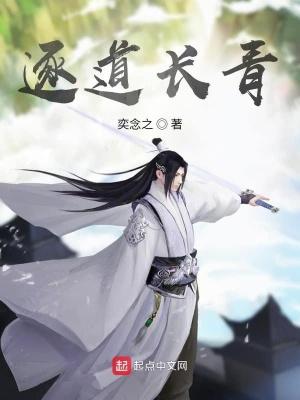秃鹫小说>心理学专家教你读心术 > 启发式人格(第4页)
启发式人格(第4页)
老板一愣,像是久到想不起来:“十几年?我二十五,从小学就有人这么说了。”
事后,他们又去问了甄姑和郑之君妈,时间锁定在十五年前。那年,工伯当选村支书,丽姨与皲叔和好。
闹鬼传言、丽姨埋尸、赵光年信教,横贯十五年的草灰蛇线,似乎能串出些关联了。
闹鬼的事情听着玄乎,仔细一想却处处可以解释。
心理暗示虽无法强大到随意指使他人犯罪,但关乎魑魅魍魉,想暗示一群本就信奉鬼神的人,效果堪称立竿见影。
更何况这传闻有十五年之久,深深根植在村民心里。
一个信徒,从根源上倾向于相信这类事情存在,即使刚听到时半信半疑,只要加上些证据,无论物证人证,逻辑说通,很容易就被说服。哪怕不那么虔诚,或许会想亲眼看看神仙,但绝对不想撞鬼。
即使头铁不信邪,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去验证,只要心中埋下了相信的种子,那么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逃跑都来不及,几无可能追根究底地找证据。
比如卷发女人的故事,鬼村房屋老旧,首先缝隙肯定不少,风吹过狭窄的通道发出啸声,就像鬼叫。其次一堆经年的土墙,大风刮过,轰然坍塌并不稀罕。假如院子里的内墙倒了,从外面也看不出来。然而女人的丈夫一直以来受到太多暗示,认为半夜可能有鬼已经能够说明他没那么坚定,过程中难免草木皆兵。
前两个人的故事里,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哭声,只是前者说哭声嘹亮,后者只是隐隐听到。卷发女人作为转述者,描述事件言之凿凿,而第二个人作为亲历者,话语里却有许多“迟疑。
自信的证词往往更正确、更有说服力,大多数法官也是这么判定的。然而,当一个证词中有太多的细节,或是证人本身过分自信时,对事实描述的正确性反而会下降。
卷发女人好巧不巧,两个都占了,白霁不得不怀疑她说的话添油加醋,哭声更可能符合后者说的情况。
而第三个人提到的送子观音,会不会是抱着婴儿的丽姨?如果是,她为什么会连续两天半夜抱着孩子在外面,也是埋尸?红光和白烟又是怎么来的?这些暂时不能确定,还得去现场看看。
无论如何,三个证词相互映证,至少能说明这哭声大概率源于孩童啼哭,并且事件至少十年间一直存在。
白霁始终认为,赵光年的痛处不在那些广为人知的事上,而应该更为私密,更为小众。他混的圈子,虽然不太体面,但没到牵扯人命的地步。一桩长达十余年、涉及多个婴儿的埋尸案,完美符合关键痛点需要的条件。
搜索赵光年参与的公益项目,给山区儿童捐款至少占一半,这些大概就是赎罪券吧。
她心里还有些猜测,比如十五年前那场饭局,赵光年是否和丽姨达成了某些交易?那天赵光年的电话对面是丽姨吗?可那天她就在村里,明明可以约个没人的地方见面。不至于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打电话避嫌。
又或者,达成交易的不止他们两人。如果是远在外村的花婶,或是常在县里跑的皲叔,事情就说得通了。甚至能够解释皲叔和丽姨莫名其妙的和解——他们是某种利益共同体。
只有一件事费解。
他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而这个问题,也很快迎刃而解。
*
云凇明天出发回北京,但两人毕竟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晚上回酒店后争分夺秒地练习。进行完睡前聊天,关灯睡觉。
第二天凌晨五点,云凇准备出门,白霁半醒着,迷糊地回味昨晚睡前的闲聊。
霎时间,电光火石。
她从床上蹦起来,重蹈覆辙地抓住云凇的肩一顿狂摇。
“我靠!我想通了!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云凇茫然,自己都没怎么睡醒。
随后在他脸上一阵狂啄,不过她自知没刷牙,很有素质地紧闭双唇。
云凇轻轻回吻。
随后,以混沌的脑子、不该说的话,开启了两人闷闷不乐的一天。
他说:“我打算回去公开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