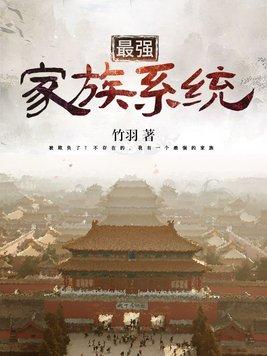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鸳鸯债歌词解析 > 白玉碑(第1页)
白玉碑(第1页)
暮时
宁王府的祠堂在别院深处,四周栽满玉兰树。春日里花开如雪,风一吹,便落满阶前。李锦期推门而入,熟悉的香气息扑面而来,那是空谷幽兰,是义母生前最爱的香,萧长敬至今仍命人日日更换。
祠堂的门无声自开,里面有些昏暗。
堂内无窗,唯有三盏长明灯悬于梁下,李锦期轻轻走进去,燃了三炷香,青烟袅袅升起,烛火幽微,在穿堂风中摇曳如泣。青砖地上泛着点点火光,却独独绕开正中一方白玉灵位,那玉极白,冷如新雪,不染尘埃,只是烟气朦胧,模糊了牌位上的字迹——“先妣端懿王妃温氏之位”。
李锦期缓缓撩起衣摆,对着那方灵牌端正跪下。兰香缭绕间,她俯身三叩首,衣袖垂落于地,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她俯下身子,静默良久,才低声道:
“义母在上,"李锦期嗓音低缓,似怕惊扰了这一室寂静,"孩儿久疏定省,实为不孝。这些年来,每每念及义母教诲,总觉愧怍难当。如今孑然一身居于琅京,无亲长左右,唯有来此与义母说说话。。。。。。还望义母莫怪孩儿叨扰。”
香炉里面吞云吐雾,映着烛光,映得她眉目愈发清冷。她站起身,指尖轻抚过白玉牌位上细细的纹路,顿了顿,又道:“义母,我今日……见到一个人。”
语罢忽地噤声,仿佛连呼吸都放轻了,只余门外乱影婆娑,沙沙作响。
话一出口,又觉得可笑。她与商时序不过两面之缘,何至于特意来与义母说?可心底那股莫名的情绪却挥之不去,像是幼时吃多了糖,舌尖泛着甜,却又隐隐发涩。
她抬手抚过供桌边缘——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她七岁那年偷偷爬上来拿供果时不小心划的。义母发现后,不仅没罚她,反而笑着捏了捏她的脸,说:“陶陶若是饿了,直接与义母说便是,何必偷偷摸摸的?”
那时,她刚被接到宁王府不久,边疆那整日刀尖上讨生活的阴影还未散去,她整日缩在角落里,连话都不敢多说。是义母一点一点将她拉出来,教她读书习字,背诗作画,带她逛花市、放河灯,给她做糕点,喂膳食,甚至在她生病时,整夜守在榻前,哼着悠悠小调哄她入睡。
李锦期闭了闭眼,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袖。
“义母,我今日……突然很想吃您做的玉兰酥。”
她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娘亲不会下厨,也没空下厨,就是有空,做的点心也是又硬又咸。”
“可您不一样……您总是做我最爱的口味,酥皮薄,馅儿清甜,还撒上桂花蜜。”
“您走后,我再也没吃过那样的点心了。”
窗外的风忽然大了些,玉兰花瓣簌簌落下,有几片飘进祠堂,落在供桌上。李锦期伸手接住一片,花瓣柔软,像是义母曾经抚过她发顶的手。
她低头看着掌心,忽然笑了笑。
“义母,您若是在,一定会笑话我吧?”
“不过是见了个陌生人,竟胡思乱想了一路。可是我,实在是没人能说这些,您就当做听着解闷吧。”
“不过他泡的茶倒是好喝,用的乌居雪芽。。。”李锦期忽然哽住,想起义母生前总爱在廊下煮茶,说她“陶陶喝茶像小猫,非得吹三下才肯喝”。
门外,玉兰树的影子被光线拉长,斜斜投在地上。李锦期望着那影子,忽然觉得,义母若是在,大约会温柔地摸摸她的头,说:“陶陶,心里若是有疑惑,不妨再等等看。”
话到一半自己先笑了。窗外暮色渐浓,玉兰花的影子又投在里面的青砖地上,恍惚间像是义母生前最爱穿的那件月白襦裙。
祠堂外,夕阳渐沉,暮色染透了半边天。李锦期静静站了一会儿,才惊觉铜镜还在身上,她轻轻叹了口气。
明日……还是去还给他吧。
祠堂外,萧长敬立在玉兰树下。他本是来寻人去问罪的,却在听到李锦期说的话时停住了脚步。
夜风卷起他官袍的下摆。
不一会,萧长敬转身时踩断了一截枯枝。祠堂里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快步离去,背影融进渐深的暮色里。
她把铜镜仔细收进袖中,轻轻摸了摸那块玉牌,动作小心又温柔:“明天我再来看您。”
“陶陶一直记挂着您。”
回廊响起脚步声,晚膳时分,李锦期回到自己的小院。丫鬟已备好了饭菜,见她回来,连忙出去迎接。
“小姐今日怎么回来得这样晚?世子方才还问起呢。”
李锦期一怔,向屋里一看,萧长敬正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哥?”她诧异地看向首座。
萧长敬头也不抬,专心吃饭,把一碟点心朝着她这边放过来:“厨房试的新方子,你尝尝吧。”,桌上正摆着一碟玉兰酥。酥皮烤得金黄,上面撒着她最爱的桂花蜜。萧长敬在她伸手拿点心时补了句,“洗手去。”
李锦期嘟嘟几句过去洗完手,再过来时小心翼翼问道:“怎么,你生我气啦?”
萧长敬看她这样子,心里有火也不能乱发,他问:“你今天把人甩干净,做什么去了。”
李锦期道:“我今日只是想自己逛逛,我知道错了哥,你别和师兄说。你天天派人跟着我,我又不杀人放火,我又不是囚犯,你那么不放心干什么?”
萧长敬又想起来她那句:“可是我,实在没人能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