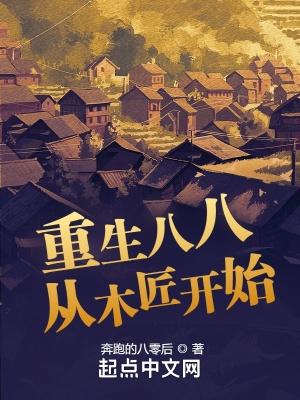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苦雨初霁 > 全1章(第1页)
全1章(第1页)
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男人坐在沃尔西尼街边享受咖啡和报纸,悠闲的午后令人舒适。
叙拉古的雨季总是充斥着不尽的细雨,教人不清爽。
却也是好事一桩,至少咖啡厅户外的桌椅不再有多少客人,也算雅致——那是平常。
此时,看报男人身边空着的座位里,身穿黑西装的人们陆续落座。
坐满了,后面来的便索性站着。
而街对面的披萨店门口也发生着大差不差的事情,不过聚集起来的人们身穿白色西装——是家族的对峙。
叙拉古平民自有一套生存之道,看报男人识趣地站起来走向店里。
黑西装们为一个矮小却精干的鲁珀男人让开道路,他不急不缓地坐上还带着看报男人体温的座椅,点上一支雪茄。
看报男人顾不得撑伞,当他走出户外遮阳伞,几滴雨水胡乱地落在他手中的报纸上。
看报男人进咖啡店门时顺手带上了锁,拖着发软的腿,耷拉着他的鲁珀尾巴小步向前。
他应该是要逃离身后那扇并不结实的门,却又本能地怕发出任何声响,几步踏出方才长舒一口气。
街对面的披萨店学着咖啡店店主将门窗的金属卷帘拉下,黑西装的精干鲁珀熄灭手中的雪茄——
虚张声势的喊杀声和金属碰撞之声从门外传来,看报男人不敢确认外面发生了什么,却也不必看便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这就是叙拉古的日常。
他在店堂里一群同样面露惶恐的避难客人中寻了个空位坐下,试图继续每个正常午后都该有的看报活动,自欺欺人。
深色的湿痕在纸面晕开,没个重点地给今日新闻胡乱批注,他一个字都看不进。
一个白西装的弩箭射穿了咖啡厅的窗玻璃,随后威力不足的箭矢就这么嵌在了内侧的金属卷帘上。
一个手持短刺的黑西装被踢飞,撞碎披萨店门口的户外餐桌后重重落地。
最近的叙拉古大小家族们仿佛集体开了窍,底层打手们总算晓得在那身廉价西装内侧塞块钢板以保护自己免受致命伤。
弩手们开始卖弄着手上粗劣的源石技艺,天花乱坠地谈论邻国莱塔尼亚的新款施术单元——他们总是这样,一只脚迈出去试图追赶时代,一只脚留原地甘愿固步自封。
雨小了些,像是什么预兆,但激战正酣的黑白西装们不理会——直至远处钟楼里落下五声钟响,越过雨幕,掷地有声。
时间停止了一瞬,方才还扭打在一起的家族成员们各自分开,或自行移动,或被同伴拖着回到了各自那侧。
双方的为首者不约而同地望向远处法院的方向,随后互相对视,带着各自手下转身离开。
家族无疑象征着暴力,人们以文明之名规训暴力。
因而在诞生于文明之上的城市中,家族便是恶。
一场就结果而言点到为止的火并方才结束,恶狼们忙于回到自己的家族,指着身上新添的伤口向同伴吹嘘一场并不存在的你死我活。
而正义——
五点是拉维妮娅法官下班的点,她一手打伞,一手持法典,踏过阴云下的街道。
雨点落入街面深浅不一的水塘,女法官法袍的倒影支离破碎。
她看见对门开的一家咖啡店和披萨店早早拉上了卷帘,损毁的露天餐桌和被弩箭射穿的橱窗玻璃。
两家店门口各放着一沓钱,浅浅的血迹顺着雨水流入下水道。
叙拉古的雨季总是承担着一部分为家族火并善后的职责,而两位店主则会拿着家族留下的钱重新装点门面,大家心照不宣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正义总是迟来一步,黑与白在这片土地上维持着可笑的“叙拉古式融洽”,粉饰太平。
拉维妮娅皱眉,镶金短靴将一个硬物踩入地砖缝里,那是某个不知名打手在火并中遗落的家族徽记。
她没有低头,只是像往常无数个下班一样,径直朝家中走去。
“叙拉古的律法不过是一张冠冕堂皇的画布,任他们再怎么装点法院华贵的门面,在法院门口那巨狼雕像——口中叼着的天平上如何加码,都改变不了这个国家地上地下两套体制并行的事实。”
这是拉维妮娅经常说的话。
对同僚,对朋友,也曾对好勇斗狠的家族成员挺直腰杆如此说过。
而如今,叙拉古的新城邦已在航道,家族不被允许染指它,平静得不像是叙拉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