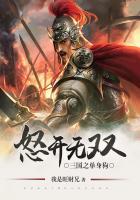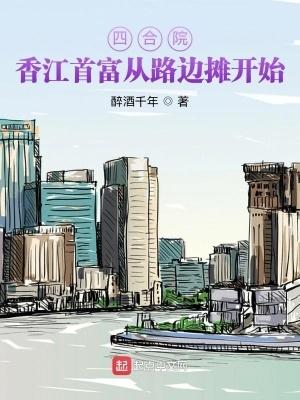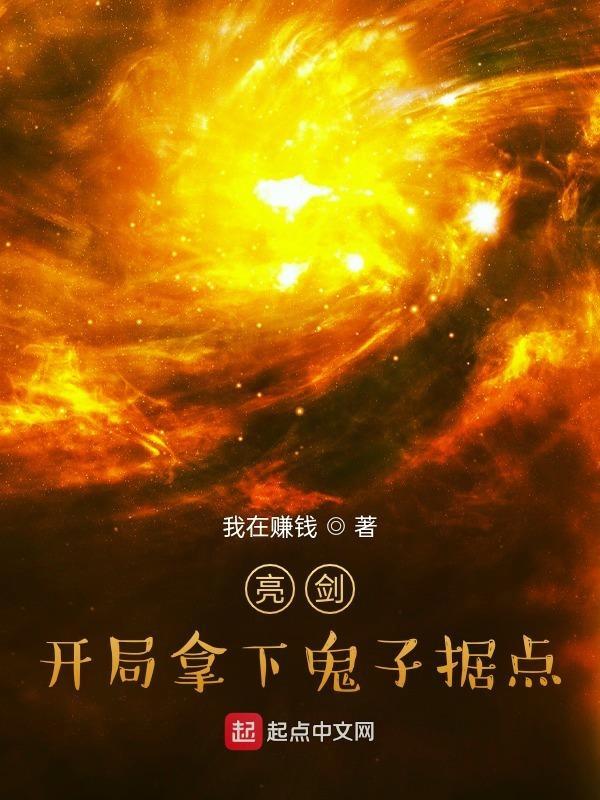秃鹫小说>冒姓琅琊在线阅读 > 第244章 话题(第2页)
第244章 话题(第2页)
这边被王扬“救起”的话题还在继续:
“。。。。。。毕竟是太原王氏,门第在,所以能做太子舍人,只是家底太薄,听说曾因家贫乞小郡。。。。。。”
席恭穆突然插话说:
“其实太原王氏的嫡系正枝,也有贵盛的。”
众人疑惑地看向席恭穆。
席恭穆神秘一笑,向北指了指。
众人都是一副了然的神情。
殷昙粲有些感慨:
“那边是王愉那一支。当年宋武帝杀王愉一家十余口,只有王慧龙一人逃到北边。此人为了报仇,降了北虏,屡引兵与宋战,檀道济、到彦之、王玄谟诸将,皆不能敌。武帝曾施反间计,失败后又遣刺客,以‘二百户男、绢一千匹’为赏,购王慧龙人头,亦不能成。伪帝授王龙骧将军,赐爵长社侯。这才是太原王氏的真正嫡宗!只可惜呀,投了胡虏,直到死也不能归葬江南。”
殷昙粲惋惜摇头。
席恭穆不以为然地一笑:
“人家太原王氏郡望就在北方,死了不葬晋阳,也葬河内,何必回江南?”
在场的士族琅琊王、淯阳乐、安定席包括他陈郡殷,都是祖上南迁过江的侨姓高门,东晋初年时,即便死在江南,也多有“假葬”者(即临时葬),意思等收复中原之后,还要迁回北方祖茔。但随着时间推移,后代久居江南,祖上几代人都葬于此,以前的权厝之所,反而被当成“祖坟”,所以才会有殷昙粲“归葬江南”的话,其实如果溯源返本,所谓“归葬”之说,本来就是不成立的。
殷昙粲立即反驳道:
“不然,礼以顺人情为本,孝以奉亲安为要。如今北土陆沉,先人丘陇早沦为腥膻之地,今我辈五代以降,坟茔皆在江南,岂有不依父母居而别寻的道理?”
话题渐至敏感,席恭穆没有再与殷昙粲争辩,闭口不言。殷昙粲也不说话了。气氛顿时有些冷场。
王扬开口道:
“王慧龙心心念念要学伍子胥回来报仇,放出话说要‘鞭尸吴市,戮坟江阴。’至于葬在哪对于他来说,或许就没那么重要了。不过我听过一种说法,说他不是王家血脉,而是僧彬与婢女私通生的孩子。”
王揖神色微动。
乐湛附和道:
“我也听说这个传言,说僧彬本王家仆,其子鼻大,颇类王家齄鼻之相(宽大鼻,酒糟鼻),遂携子北奔,诈充遗胤。。。。。。”
殷昙粲冷笑一声:
“一定是谣言!太原王氏这种甲门贵家,外人根本冒充不了。。。。。。”
王扬点头,一副深以为然的模样。
王揖低头,小口喝酒。
殷昙粲声音忿忿:
“。。。。。。此乃索虏妒我华胄清流,故设谤语污之耳!当年崔浩不过夸了一句王慧龙‘真贵种矣’,便有人向伪帝谮毁,说崔浩‘叹服南人,讪鄙国化’,伪帝怒,召崔浩责之。浩免冠陈谢乃解。可最后崔浩还不是被灭族?可见北虏夷狄本色,嫉我华夏衣冠,凡能毁之,无所不用其极!王慧龙娶清河崔氏,子聘范阳卢门,女归陇西李家,凡所通婚者,莫不是北土一等望族,如何能有假?!”
王揖目光悠远,声音沉了几分:
“的确不是假的。王慧龙北奔时是十四岁,那年我祖父正好十岁,见过王慧龙,还说过话。后来王愉被灭家,只剩下这一个血脉,被与王家常往来的沙门僧彬藏了起来。他们是先跑到江陵,然后北上襄阳渡江,自虎牢奔姚兴,姚兴败了之后才转投的魏虏。当时听说王慧龙跑了,全江封锁戒严,朝廷下令,见面格杀不问,就是怕他跑到北边去。没想到还是被僧彬护送走了。若没有僧彬,就没有王氏遗孤,我以为,僧彬之义,与古时程婴等。。。。。。”
众人正闲谈间,忽有一仆上前,呈给王揖一封信。王揖读后,笑道:“原来谢家雏凤也在荆州。”随即看向王扬:“贤侄,你可是曾请谢四娘子引见,拜访慧绪师太吗?”
王扬欠身答道:“是。侄儿早想谒见慧绪师太,一来是要请她诵经为先父再荐冥福,以尽追思之念。二来是想借此机会,请教一下佛法。可师太不见外客,所以只能托谢四娘子代为求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