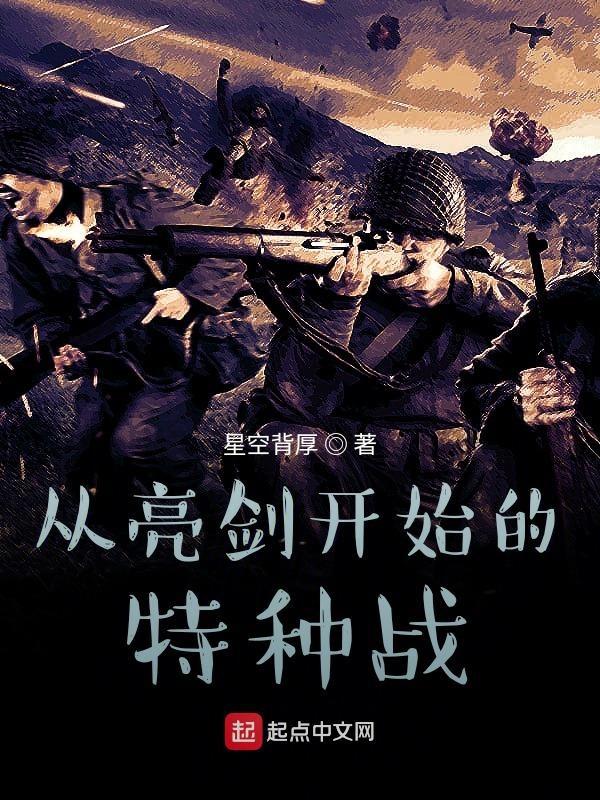秃鹫小说>沾洲叹by诗无茶不洁吗 > 第77章 77(第3页)
第77章 77(第3页)
容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又觉得祝神根本听不进去,干脆不吭声了。
祝神举起手,缓缓从剑的顶端摸到剑尾,忽然从床头取下剑:“把它也带上。”
自打目睹祝神那晚杀人后,容晖对这剑天然生了股忌惮,仿佛它是什么邪物。他总是要把那夜祝神癫狂的原因归咎在其他什么东西身上,兜兜转转便是这把剑最合适,否则容晖便无法宁静,难以自抑地去思索变成邪魔的究竟是剑,还是祝神。
他久久没有接过,祝神的声音也冷淡下去:“你害怕,就让刘云上来。”
祝神还是那个祝神,不动声色洞悉着每个人眼底的想法。只是以前的祝神是收纳百川的水,如今却成了横指千峰的剑。
容晖抬手接过剑,正要往箱子里放,又听祝神说:“收进夹层,别让人一翻就看到。”
去猎场的路上祝神依旧是补觉,贺兰府的人马在前,祝神的马车在中末端,时不时会有骑卫驾着马下来给他们送水送点心,行至一半,大军驻扎休息,祝神没胃口,吃了补药便不肯进食。容晖正发愁,贺兰破端着煨好的山楂汤过来了。
好不容易喝完汤,祝神兴起吃了几口点心,便说下车透透气。
正站在草地上晒太阳,辛不归从远处骑着一匹快马过来,屁股后跟着醉雕。
马是贺兰明棋才赏的烈马,辛不归训了几天,终于驯服帖了,去猎山的路上都要骑着跑几圈。
离他们近了,辛不归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坐骑一手带着醉雕,高高举着手给他们打招呼:“公子!”
祝神含笑招手,他便跑过来了。
醉雕照例是要往祝神身上扑,贺兰破一眼瞥下去,它低头舔爪子,当作什么也没发生。
“吃点东西。”祝神顺手把盒子里的点心递过去,看着辛不归两口解决一个,又递了一块,“这就是你那匹新马?”
辛不归擦了擦汗,嘴里忙不过来,便睁大眼睛直点头。
祝神一看见他心里就欢喜,像看见自家养的孩子——其实他与贺兰破也没什么区别,这么多年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祝神派人暗里守着贺兰破,就是守着辛不归。他等辛不归吃完,又亲自递水,全然没注意贺兰破已经朝他看了好几眼。又问:“骑马好玩吗?”
“可好玩了!”辛不归咽下水,叽叽咕咕说了半天这马的了不得之处,最后又道,“我最喜欢骑马了!像在跟风赛跑一样!祝老板你有机会的话,真该试试。”
这话不知戳中了贺兰破哪里的忌讳,辛不归再没眼见,也感觉到对方突然将两道凛然的目光投了过来。
再一看,贺兰破又低着头在摸醉雕的脑袋,刚刚那一幕恍若什么都没发生。
祝神面色倒是没有波动,只是将视线长久地凝固在他身后那匹黝黑的骏马身上,末了微微一笑:“我骑不了马。太颠了,受不住。”
辛不归怔了怔,抠抠后脑勺:“我忘了……您不会骑马,真对不住。”
冬日朝晖的微风里,祝神只是笑,没有接话。
在上路时,贺兰破与辛不归并肩而行。
两个人高居马背,静静行驶在大军之中,一时无话。
过了很久,贺兰破突然开口:“他会骑马。”
辛不归猝不及防:“啊?”
贺兰破垂下眼睛,重复道:“祝神当年,也时常骑马。”
他顿了顿,又说:“为了我。”
为了给他求药,祝神也曾跋山涉水,俯仰唯唯,策马追风到破晓。
他没忘,祝神也没忘,只是谁都以为对方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