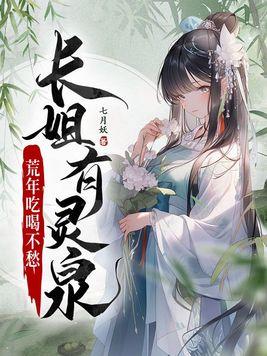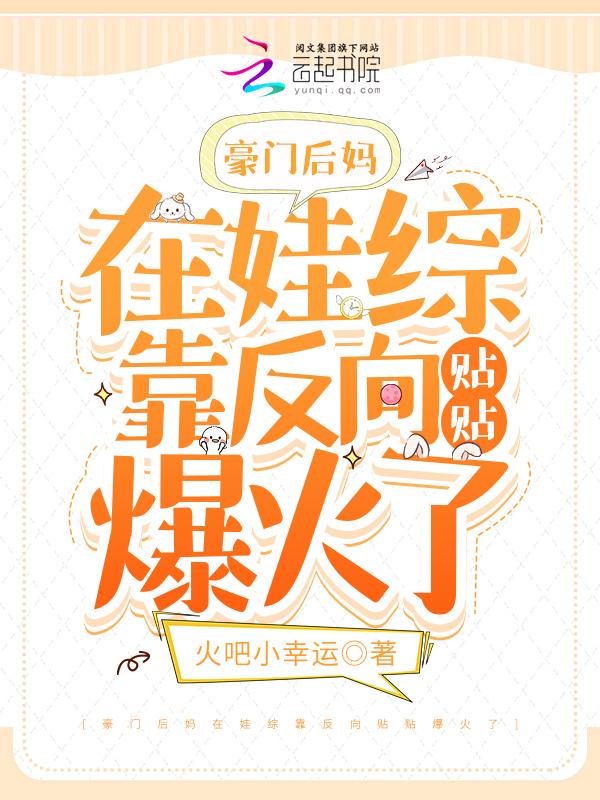秃鹫小说>菟丝花女配快穿格格党 > 第731章(第1页)
第731章(第1页)
新的环境,新的工作,阮柔在陌生的地方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而阮家那边的消息,也不时通过柳芝芝的信件中展现。
什么她嫂子郝春红如愿给阮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喜得阮父给一栋楼里每家都送了个红鸡蛋,这可不是小手笔。
当然,阮父虽然喜欢孙子,可照顾孙子的活还是落在全家唯一的闲人阮母身上。
没有工作,挣不到自己的工资,阮母的腰杆不弯也得弯,更何况还有阮父在旁一直压着。
不过,阮母也不是个任人欺负的,孩子刚满三岁,她就给送去厂里的育红班,而她自己则花钱买了个临时工,重新开始工作。
买临时工的钱就花了四百多,按照一个月二十的工资,也得近两年才还清,而且,这就是个不能转正,不能落户的临时工,可以说,从价值上来算,并不划算。
可阮母就咬死了自己必须去上这个班,否则,就算待在家里她也不会忙活家里这一摊子破事的。
从儿媳郝春红怀孕自己被迫让出工作,到孙子终于三岁,期间足足四年时间,她可谓受够了。
什么叫吃力不讨好,什么叫人心隔肚皮,总而言之,阮母最终只认定了一点,什么孝顺丶什么儿子孙子儿媳,什么传宗接代,都是虚的,只有自己工作挣到手的钱才是真的。
因着阮母的坚持,所以哪怕阮父乃至阮之江丶郝春红都不乐意,阮母这个工作还是顺利买下来了,用的是家里辛苦多年存下来的积蓄。
其实以阮家如今三个人工作的工资,家里还真不怎么缺这二十的工资,反而,家里有个能照顾里外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自从阮母撂挑子不干,阮家就险些乱成了一锅粥。
衣服,阮母只洗自己和阮父的,问就是阮父养家工资还高,儿子儿媳的衣服自己洗,做饭一天三顿里只做一顿晚饭,早上随便对付两口,中午吃头天晚上剩下来的,还直接在厂子里吃,中午连家都不回了。
她一个人这么做可以,可阮家还有三大一小四个人,总不能都这么干,所以,中午那顿饭,多半是郝春红做,阮之江进厨房帮衬,至于阮父,作为家里的挣钱支柱,阮父家里的活依旧半点不沾。
如今,阮母最羡慕的人,除了早早离开家,据说在外过得很是潇洒的女儿,就最是羡慕阮父了,万事不操心,最后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自己赚钱才能踏实。
阮母不用为家里费心,宁愿将满身的力气挥洒在岗位上,反而使得她倍受小组长赏识,虽然年纪大了点,虽然是个临时工,可人家干活肯吃苦用劲啊,甚至于年底还拿了个优秀工作者的奖励,可把阮母喜的。
与之相反的是阮之江和郝春红。
家里的家务活就算了,两个人分担总要不了太多时间,可关键是,两人的孩子年纪还小,放在育红班的时候没啥问题,可孩子接回来了总会闹腾,做父母的总得跟在后面收拾,费的心力比之家务活还要让人操心。
一个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家里的事忙活的多了,工作上的时间自然就少了。
而这年代又是一个特别讲究奉献自我建设大集体的时代,跟周围的工友们一比,阮之江和郝春红既不算特别聪明的,也不算特别勤劳肯吃苦的,升级涨工资自然轮不上他们。
就好似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是工资升不上去,就越得照顾家里;越是照顾家里,工作上就越没法进步,所以,哪怕时间一晃十来年,阮之江和郝春红两人的工作依旧半死不活,工资也就按照工资每两年涨上个两块钱,还比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呢。
等时代的变革来临,郝春红有意想下海经商,彼时,阮父早已退休,每日在家万事不管很是清闲,阮母则依旧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当年的临时工硬是被她熬到了转正,在岗位上退休后,她又各种找关系去给人家当保姆,总是很是忙碌,就没个闲下来的时候。
当然,阮母忙那都是为了自己忙。除了每个月往家里交的十块钱生活费,自打重新找了工作后,阮母的钱是半分不往外掏的,哪怕面对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给他们花的钱都得从给家里的十块钱生活费里扣,很是抠搜。
不过抠有抠的好处,阮母每每感觉累极了,就会掏出自己的存摺看一看,继而充满了干劲。
于是,惦记下海经商的郝春红有意想外出闯荡一番,可总被家里的事绊倒,不是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就是天气忽冷忽热下感冒发烧需要人照顾,总之,繁琐,却足以彻底牵绊住一个人的脚步。
蹉跎了一年又一年,直等到下岗潮来临,郝春红也没下定决心真正的辞职。
不过,也不需要她做准备了,因为大规模的下岗潮来了。
当初她辛苦谋划的工作,在时代的浪潮前不值一提。
先是延迟发工资,再是发不出工资,而后厂里没活呼吁大家回家各谋生路,再到后来,厂子都没了,也不过得了些一次性买断钱。
这会儿的郝春红终于不用担心这担心那,可满大街卖茶叶蛋的队伍中,也不过多了一个不显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