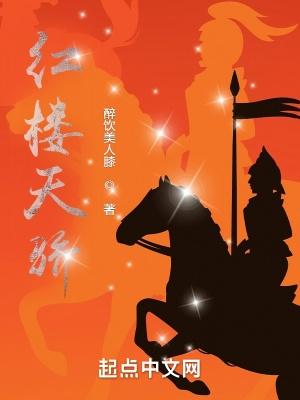秃鹫小说>农家子什么意思 > 第230章(第2页)
第230章(第2页)
直到这位客人的身影在楼梯转角处消失,几人方同时回过神。其中一人当即击掌拍案道:「此人形容气质,竟与王安抚使如此相近!」接着他笑着看向对座之人:「现在,见到方才那位客人,你总该能相信,有的人,他就是一出现,就能让你不自觉的信任他,心甘情愿被他折服了吧?」
方才还坚持自己态度的人,此时也突然没有了继续坚持的底气。
毕竟,那位王安抚使,可是从五等下户农家,自少年时代便靠着一人之力,最终直取了三元及第状元之名的超绝之人。这样的惊艳绝世之人,也许并不能以常理度之。
只是,这般风骨与风姿之人,真的有这样多?
多到他们随随便便坐在这里喝茶,都能遇见第二个?
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的再次朝着楼梯拐角的方向,望了一眼。
第194章
七月,当河东路民间的消息,慢慢传过来的时候,大景朝的京师已然进入了炎夏。
伴随着烈烈夏阳与蒸腾着暑气的高温,大景朝京都皇城的舆论,也再一次陷入了沸腾。此次引爆舆论的,除了河东路水患经调查,乃是人祸非为天灾,而一手促成这一场水患的,竟然就是上书弹劾河东路转运副使瞒报灾情丶救灾不力的太原府知府王端!
王景禹作为两路安抚使,与河东路转运副使,不仅不存在瞒报灾情的情况,甚至正是因为他在河东路期间,一系列的救灾治理灾情的措施,才使得汾水决堤口被迅速疏堵,灾区的百姓得到了最好的救助和安置。
不仅从水患当中抢救回了上万百姓生命,还使得灾区百姓面对水患的冲击之时,所蒙受的痛苦和损失降到了最低。
而原本被押解回京,扣在御史台的王安抚使,已然于半个月前被释放,同时官复原职。
至于此次恶意制造水患的首恶王端,也已经在押解回京的路上。从案件罪名成立起,王端本人就被随同调查组前往河东路的皇家禁军亲自押解看守,防止任何人与他的私下接触,以及避免他在认罪并供出其他指使丶共犯之人以前,出现意外。
也就是说,这件事王端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首恶,他的背后还有更高级别的指使之人,以及同伙!
想想这整件事情的蹊跷,的确绝不止一点半点。
当初,王安抚使被诬陷之时,王端身为河东路太原府知府,以河东水患的亲历者身份,向京师朝廷举发王安抚使;与此同时,京师这里,就有一个叫戚年的,作为王安抚使的同年,越级向皇帝呈献了一副无论谁看了都不忍直视的《河东水患灾民图》,很快的,这样一幅图的摹本,就从朝野流到了民间,使得河东路灾情之凄惨,引得人人侧目。
上至太皇太后丶皇室宗亲,中及朝野百官,下到百姓,一时之间纷纷站出来要求皇帝彻查河东水患一事。
正是这一远一近恰到好处的配合,方使得对王安抚使向来极其倚重信任的皇帝,也不得不暂时停了王安抚使的职事,并派出调查组前往河东路。
如今看来,这一切都不是远在河东路的太原府知府,可以操控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蒙冤被扣押多日的王安抚使,甫一出狱,将河东路水患全权交由了调查组继续往下彻查,自己并未继续就河东路水患一事,继续上章为自己解释添名。
而是直接请求面圣,手持四大实证,在皇宫大殿之中,当庭举告大景朝廷之宰辅蔡阙蔡相公,在当年的刘凌英刘大学士案中,恶意陷害丶伪造证据,以致刘大学士蒙冤入狱,最终家破人亡。
王安抚使提出的四大证据中,有一封当年刘凌英大学士与蔡阙之间的私人手书。
当年刘大学士的案件,曾经掀起过很短暂的热潮。但是很快,随着案件的尘埃落定,这一件事,也因皇帝的敏感以及更多人的有意为之,而被封禁,成为了从上至下禁忌的话题。
因此,对于当年案件的细节,早已经只是极其有限之人才知晓的秘辛。
这一封手书,正揭示了当时案件的一个关键细节。
当年大景朝中宗皇帝,曾经如今日的赵璜对待王景禹这般,对刘凌英有着相知相识,携手开创大景朝新局面的君臣之谊。一开始,朝野民间,都是关于君臣之间的佳话美谈。可是,当刘凌英因为祖籍太康州,其族人私下侵田三十万亩,刘凌英因为自己亲族的指证而被迫罢相入狱时,曾经与刘凌英亲密无间的中宗皇帝,却没有作出像样的为刘凌英争取的努力,反而顺水推舟,使得人证物证俱在的这一侵田案,迅速被定案判决。
根据刘凌英本人亲自设计的新法,三十万亩的侵田,哪怕他是一朝之宰辅,也要判一个死刑。
王景禹拿出的这一封手书,就揭示了,何以中宗皇帝在刘凌英的这一个案件上,突然之间态度微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