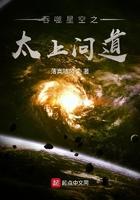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咸鱼她被迫红 > 江南好风景(第2页)
江南好风景(第2页)
惊得他立刻就出来了!
怎么是成衍。
张贺年这官做得真是有水平。
乱头粗服不可见君王,本想回屋梳洗一番,想想又抬脚走了过去。
这不是在宫里,他守了半辈子规矩,现在一点都不想守规矩,更何况阮阮还在那坐着,怎么能将家妻单独扔在虎狼之侧。
成煦走到阮阮身边的蒲团坐下,附在阮阮耳侧,轻轻说道。
“小满在找你。”
阮阮瞧了他一眼,领会了他的意思,起身回了屋。
“皇兄,别来无恙。”成衍见他没有说话的意思,习惯性地先开了口。
成煦摇摇头,“成王已经身死,薨逝的讣告早已遍及四海,陛下不要如此称呼。”
从去年入秋后,成煦就在筹划出京下江南,他上了一份罪责书,自请挂印而去。
但这封奏折被成衍留中不发,他不敢批,也不知该怎么批。
既不想放,也不想留一个处处掣肘自己的摄政王。
后来成煦又递出一个台阶,彻底放弃皇家的身份,并且把西北军权交出来。
他犹豫了,可他凭什么信他?
直到他将一个攒丝祥瑞的楠木盒子给了自己,里面是母后的亲笔手书,还有先太子的一封信。
他才知道,自己并非先帝的儿子,而是先太子的儿子。
这样的身世秘辛他竟然藏了这么多年。
当年他若将此公开于世,皇位唾手可得。
“你想过当皇帝吧。”
成煦喝了口阮阮没喝完的茶水,“太子倾尽心力庇护、教导我,大厦将倾时却冒着被父皇忌惮怀疑的险,将我从京城摘出去送往西北,你说我该当这个皇帝吗?”
“先帝明发诏令,传位于你,我若抢了,就是万古不易的贼。”
“我不能让阮阮和小满跟着我被遗臭万年。”
成衍低眸沉默。
“陛下是后悔放我走了?”成煦又倒了一杯茶,半阖着眼品茶。
成衍瞧着他这副与在宫中截然不同的懒散做派,是故意做给自己看,还是这才是他的真性情?
“朕是得了阿姐的消息,来见她,”他像是堵着一口气,硬硬地道,“不行吗。”
言下之意,不是冲着他来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自然来得,只是你的阿姐看起来并不想见你。”
“陛下若还怜惜昔日的那一点姐弟之情,还是不要来的好。”
“毕竟她怜惜的也不过是幼时的你。”
小嘴巴巴地十分能说,说出来的话就跟淬了毒一样,专门往人心窝肺管子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