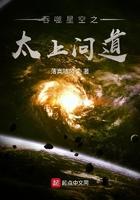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老婆不是cra > 22第二十二章(第2页)
22第二十二章(第2页)
不过木刻的一块牌子,哪里是什么值得随时戴在身上的东西?可他竟然时时戴着。
谢相呴不由喃喃:“我还以为你扔了。”
李宿却摇头:“这是为你求的平安牌,不会扔掉,其实我前几天才找到。”
李宿为他求的平安,他希望李宿也平安,可事与愿违。
……他能不能做些什么?能不能再多做一些?哪怕给李宿片刻的平安?
谢相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李宿则收好平安牌,继续垂头看书,等待着学堂学子陆陆续续地到来。
“我还以为你死了。”再过一阵李吉星到学堂,见了李宿也是惊讶,但见了他案桌上放好的近几日的课业,当即便嗤笑出声,随手拿起一张:“要我说你学着有什么用?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字也丑得不堪入目,不如早点滚回丹州放羊。”
李宿并不回答,但李吉星因他的沉默更生气,干脆将手上那张课业攥成一团扔出窗外,又将案上的课业一一拿起,撕了个粉碎,而至此,李宿依旧没有任何反抗,只将地上那些碎屑一一拾起。
至此,李吉星终于满意。他躬身之际,李吉星踩在他背上,道:“以后你的课业干脆都拿来给我撕吧,记住了吗?你这样的东西,就不必拿去脏钱父子的眼睛了。”
至此,李宿对他的一干举动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他点点头,答:“好。”
钱夫子到后,果然向李宿问这几日的课业,“昨日差人给你送了书补上,可都写了?”
学堂众人一时都望向他,谢相呴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望着他。
他的那些课业早被李吉星撕了个干净,只剩一张落在院里成团,自然拿不出来,但尽管如此,还是实话实说,道:“做了。”
钱夫子颔首:“呈上来老夫瞧瞧。”
这时李宿安静下来,也没有任何动作,半晌才道:“学生的确写了,但拿不出来。”
“这是为何?”钱夫子问。
在这个瞬间,谢相呴听到一声嘲弄的笑低低响起,含着毫不遮掩的恶意,发出这笑的李吉星道:“李宿,你可不要骗夫子。”
“静。”钱夫子闻言提醒,再度看向李宿:“没写便没写,写了便有那课业。此事虽小,但李宿你往后对人不能再有欺骗之意。”
这便是认定李宿没有写的意思。
“夫子所言,学生铭记在心,”李宿垂眸,而后又抬起:“可写了便是写了,学生真的写了,没有骗您。课业也的确是学生无法呈交,请夫子责罚。”
钱夫子轻叹一声,而后令李宿上前挨戒尺。
因他七日未来,七日的课业未交,便实打实要打七下,钱夫子下手并不轻,雨声里都能听到戒尺破风拍下打到掌心的声音,可李宿连眉头都未曾皱起。
打到第三板的时候,谢相呴并不再看,侧头将目光移出去。
那团纸早就彻底晕湿,透了点点黑色淡墨,又被雨水冲散。
李宿写了,他知道的。
他知道李宿一贯认真,从开始的一字不识到现在能写完课业,他也知道李宿没有欺骗,从来都是诚实说话。
可是他甚至不能开口为李宿作证,因为那样只会让李吉星变本加厉,不知他下次还会有什么手段对付李宿。
可是为何要如此?
为何他连这样的事都做不到?
为何他生下来便是这样的身体……为何他生在大齐这样灰败的时候,为何平宣侯府也落魄?要将他许给李家?为何李贞那样的人都能常伴官家身侧评论国事,令整个文信侯府为虎作伥,霸道横行,而真正的忠臣良将却只能沉默,还要流放千里?难见君颜?
为何明明李宿并没有什么错,却要遭受这些?
为何他明明只想要一点自由,只要那样一点,都要受尽阻拦?
……
一滴泪水顺着他的面庞滴落到紧攥的手上,钱夫子的戒尺仍然未停。
李宿的手已经被打到发红,他依旧一声不吭,并不叫疼。
谢相呴攥紧手,从未有过的恨意忽然从这潮而阴沉的天气中生根发芽,只经这一滴泪灌溉,便迅速生长,其意汹汹。
既然平安牌是假的,庇佑不了李宿,那么就他来做。
他来让李宿平安。魔·蝎·小·说·MOXIEXS。。o。X。i。exs。&